源自乙太
前篇故事:首席亂匠
吉拉波的乙太種是個充斥著尋樂者與腎上腺素上癮者的種族。壽命最長只有四年,他們將這座城市視為他們天然的棲息地,而派對則是他們的遊樂場。雖然他們的生命短暫,但他們仍具有能夠體會周遭人群能量的共感能力。
耶赫尼,一位發明家,慈善家,以及社交名流,知道他們的生命已來到尾聲。當他們在發明家博覽會前面舉辦了其中一場極為奢華的派對時,竟有三位不速之客前來探求危險的知識。

一
我熱愛在午後盛裝打扮。從中午就開始為熬夜一整晚做準備有許多好處,尤其當到了最後一刻才決定要參加一場派對時,可能會失去某種程度的先見之明與準備工作。我不是從兩小時前才開始打扮-我從兩天前就開始打扮了。
哪種主辦人看起來就像是在他們自己的派對裡折騰了十六個小時的一團髒亂?失敗的的主辦人。就是那種。
午後的陽光穿透我私人房裡的窗簾,照亮了佔滿我最大面牆的那些純金浮華品。滲透進來的光線不停閃爍,而珠寶、裝飾品,以及豐富珍寶上的黃金正從每個抽屜裡往外窺探,在巨大箱子的每一個表面上閃閃發光。我是乙太種;我知道自己將於何時死去並且我知道自己在那之前要過怎樣的人生,而且我不會把時間花在那些認為我不值得讓自己看起來賞心悅目的白痴身上。
就在我戴上我第二喜歡的胸針時,我幾乎能聽見樓下派對員工的騷動。伙食承辦人正在好好地利用我的廚房-有機生物對他們的食物非常挑剔。幸好我的伙食承辦人,奈維德,從沒讓我失望過。他現在正在廚房裡辛勤地為那些擁有胃部的人們備餐;一座棕櫚酒噴泉,一盤又一盤的咖哩角、空心脆餅、茄香咖哩,以及擺滿了一張大桌的甜點(優格面前總是大排長龍,所以那一定很好吃)。我其餘的員工現在正忙著組裝屋頂的頂蓬。在那些厚實疲憊的遊園群眾躺下歇息之後,我和我的乙太手足們將在夜色中舞蹈,直到天明,直到下一個夜晚,陶醉於歡慶的狂喜之中。
但那是之後的事。在考慮了二又四分之一秒並在我的奢華品堆裡胡亂翻找過後,我決定在今晚使用這瓶灌注了茉莉香與乙太的精油。這是我個人的最愛。我的映象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感到沾沾自喜。我看起來還不到三歲呢!
甚至在底下這裡我就能夠感受到屋頂上派對員工的歡欣激動與那瀰漫著檀香味的期待。我開始憐憫其他無法體會我們感受的種族了。當我的族人在五十年前首次從早期乙太提煉場裡爬出時,他們稱之為「共感共鳴」。「一種能夠精確地感知到周圍生物的情緒狀態的奇特能力。」他們將發明我們的功勞歸於自己,卻從沒想過是我們創造了自己。我悲哀地笑著。從那時起我們唯一發明的東西就只剩下自娛自樂的方法。
當我把精油沾在我的手腕與脖子上時,我看著我的一小塊皮膚消散成一縷清煙。隨著更多堅硬的皮膚消失,我也就愈接近生命的終點。我可以看見藍色的乙太在裂隙底下流動著。我深深著迷於它的美麗。它好迷人。一種要我加緊腳步的溫和提醒。我用額外的一條手環蓋住了裂隙。
我的族人天生就能夠意識到時間的流逝以及我們每個人還剩多少時間。就像是在等一班列車。每個噪音都會使你抬起頭,而且每一陣強風都會讓你變換座位,但車子卻還沒抵達。
我已盛裝打扮,散發著微光並且準備就緒。我還有五十四天可活。
二
適切地打扮之後,我走上通往屋頂的階梯並撞上了嘈雜的聲響。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比得上被派對音樂那堅固的手直接砸在臉上的感覺了。
頂蓬在由我的員工從樓下拖上來的奢華地毯上投映出一道歡迎的陰影。裝潢設計師在桌上擺了木蘭花,將它們垂掛於建築物的側邊,而美麗的絲線則沿著欄杆延伸並裝飾著在午後陽光中閃爍的絲金。我在行走的同時輕易地斟滿了空酒杯,躲開了兩個接吻的人類(我笑容滿面地看著這一對。我在上一場派對裡湊合了他們兩個-把我的能力用在行善上總是好的),帶領矮人們前往廁所,並調整了家庭型號萬和琴的音量。
忘了物質與腎上腺素-派對是最棒的惡行。我享受著賓客們的感官享樂。我不知道大啖一隻烘烤動物的感覺是什麼,但我想像著類似那樣的感受。我沉浸於主辦人的職責裡,而我的賓客們都讚不絕口。
我的摯友兼王牌駕駛德珀拉(就是那位德珀拉!)正輕鬆愜意地坐在一張更為隱密的長沙發上。她的鬣狗坐在她身旁,正快樂地啃咬著一根骨頭,而德珀拉則在玩弄著一條金鏈。
「德珀拉,親愛的,我的派對因妳而變得更加耀眼了,」我誠摯地擁抱她,並彎下身疼愛地搔了一下鬣狗的耳背。這隻鬣狗用鼻子輕推著我的手。
「她很喜歡你呀,耶赫尼,」德珀拉帶著信賴的笑容說道。「在退休後找時間放鬆一下嗎?」
「某人的消息還真靈通呀,」我一邊斟滿她的酒杯一邊斥責道。
「通常只注意比賽結果,不過我也會篩檢商業消息呢。」
我的家族透過投資而獲利。當我一發現自己還剩不到六十天可活的時候,我立刻就宣布退休。當你無法活著看見結果時,大膽的投資策略將會更容易執行。
我在她身旁坐下。「那麼我猜,妳將會在一個月內參加我的倒數第二場派對吧?如果沒有吉拉波最棒的駕駛參與,那將會變得極度無聊呀。」
德珀拉露出笑容,心不在焉地用手輕拍著她的鬣狗。「我不會錯過的。乙太種的習俗最棒了。」
「我由衷地同意。我們只不過是及時行樂罷了,親愛的。」
德珀拉的表情變得嚴肅。她用視線來回巡視任何可能在一旁偷聽的人,同時皺起了眉頭,「所以…你不打算延遲嗎?」
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憤怒。
「我知道你的能耐,耶赫尼,」她帶著意味深長的表情說道。
「我不想談得這麼深入,德珀拉。」我揀起手臂上那逐漸崩解的皮膚。我知道自己能夠吸取精華已經有一段時日了,但我並不想使用它。它是一種罕見的天賦而且最好不要將它表現出來。我不能只為了要讓自己活過死期就把生命力從另一個具有意識的活物身上偷走。我的朋友們將會如何看待我?
「那是一個選擇,」她漫不經心地說道。「我不知道它是如何運作的,不知道你能夠從…其他人身上得到多少時間。我不確定你是否會考慮這個方法。」
「曾經有過這個念頭,不過我想要以傳統的方式離去,」我強迫自己這麼說。
就在那一刻,奈維德,我的伙食承辦人,帶來了一瓶德珀拉最喜愛的飲料。真體貼呀-他幾乎就跟我一樣美好。
「你是個好人,耶赫尼,」德珀拉在我們回復獨處之後說道。「多活幾天並不值得你這麼做所帶來的罪惡。」
我不確定她說得對不對。
三
有三個女人站在我的公寓入口處。我立刻就認出了帕西理夫人(世界上最著名的發明家之一,同時也是我所認識最為激進的桌上遊戲狂熱者)。在她右邊的是一位身穿過時披巾的年輕紅髮女子(那種風格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了-難道她到異地去了嗎?)。
而站在另一邊的則是我這輩子見過最令人著迷的人物。
她的雙眼沒有邊際,是一團由中央朝眼瞼擴散的明亮綠光,一份生動的美麗卻透露出了不安的姿態。看起來如此有趣之人竟如此緊繃,這真是一場悲劇。她的衣服上裝飾著耀眼的花朵(那些花是真的嗎?)並且剪裁方式看似只為她量身訂做。如果我對與人物談戀愛有著分毫的興趣,我將會被誘惑,但對我而言她的魅力完全是基於社交收益。當然,我身為主辦人的目標就是要讓我的賓客們盡歡,但被人看見與有趣的人物來往總會有額外的好處。
「耶赫尼,我的朋友,」帕西理夫人說道,「這位是茜卓和妮莎。茜卓,妮莎,這位是耶赫尼。他們投資急需幫助的年輕發明家,並且也是我所知最為慷慨的慈善家之一。我們可以參加這場慶典嗎?」
「當然可以,帕西理夫人。」多棒的引介呀。我在心裡臉都紅了。
我替這位妖精撐著門。「美麗動人的雙眼,親愛的,」我在妮莎進來的同時如此恭維道。她露出緊繃的笑容。
那位紅髮女子彆扭地站在外頭。我懷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後便轉向帕西理夫人。
「那就是琵雅納拉的女兒,茜卓,」她說道。
我站到一旁以讓吉拉波最危險人物的女兒進來。「派對就在樓上,所以讓我們在安靜一點的地方談話吧,」我說。
我帶她們來到我位於一樓後側的庭院裡。帕西理夫人在我們行走的同時在我的耳邊說道。
「你知道,琵雅納拉被逮捕了。」我不知道。這對我來說很不尋常。
「琵雅不會犯這樣的錯。把妳知道的告訴我。」
我們走著,而帕西理夫人也解釋了這個情況。盆栽植物與歡欣的噴泉沿著座位空間的外緣排列,被包圍於其中的則是四張破舊的座椅。屋頂上的派對聲響緩緩流下,替我們的對話提供了絕佳的掩護。我讓她們坐下並揮手示意一位員工替我們的賓客倒飲料,同時帕西理夫人也說完了詳情。我仔細考量著琵雅納拉被逮捕的事。
「恐怕我也毫無頭緒,」我說,「我不知道執政院會把像琵雅這樣的犯人關在哪裡。」
帕西理夫人點了點頭,「我明白了。」
「很抱歉。我以利用自己的人脈感到相當自豪,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卻是條死胡同。」
我感覺到從右側傳來冒著煙的憤怒浪潮。「如果那是你的父母的話,你就會幫助我們了,」茜卓喝斥道。
「我一個也沒有,」我漫不經心地聳了聳肩。茜卓的眉頭皺得更深了。她覺得自己很愚蠢。她不應該這麼覺得-這一點也不困擾我。
我的侍者回來了,於是我便將一杯棕櫚酒遞給帕西理夫人以及把一杯木醇遞給妖精。根據我的經驗,妖精們會欣賞比較強勁的玩意-一種令我極為欽佩又羨慕的特質。
「這裡或許還有能夠幫助我們的人,」帕西理夫人補充說道,一邊用她那高雅、飽經風霜的雙手接過酒杯。
我思考著樓上的賓客並在腦中開始快速地搜索我的人脈。
突然從前門傳來一陣騷動。妮莎跳了起來,茜卓則好奇地觀望著。從我們在庭院裡的位置,我可以看見一群乙太種抬著一張椅子衝過前門,上面坐了一個正在迅速消融的乙太種。椅子上的那個乙太種渾身散發著瀕死的耀眼光芒。他們的皮膚正在消散,此刻比起實體他們更像是一團煙霧。這好尷尬啊。我把頭別開了。
「這是我的倒數第二場派對!」他們狂熱地吶喊著。這群烏合之眾舉起椅子走上樓梯,將這場生前告別式移往了屋頂。
茜卓興味盎然地看著我,「你知道它是誰嗎?」
「我寧願自己不知道,」我說,一邊抓弄著白天稍早時我覆蓋手腕之處。一道渺小的煙霧飄散。我厭惡像這樣看著自己死去。
茜卓堅決地把手放在桌上並站起身。「好了。我要開始四處打探了。妮莎-」
「我沒事,」妖精輕柔地回應。她的能量裡帶有不安的冰冷與苦澀。她真的不舒服,所以我決定介入。
「妮莎,是嗎?跟我來吧;妳一定得告訴我妳是在哪裡找到那件套裝的。」
四
我們走上樓梯,直到我們抵達屋頂正下方的樓層。我帶領妮莎來到陽台。如果在我自己的派對上有一位不舒服的賓客,那麼我還算什麼主辦人呢?
「妳看似想逃離,」我如此說道。
妖精環抱雙臂。「我沒事,」她重複著。她還是不舒服,但流露出她的好奇心,「什麼是倒數第二場派對?」
「我們乙太種最後做的一件事就是死亡,所以我們做的倒數第二件事就是舉辦一場強制出席的倒數第二場派對。如果一個乙太種沒有足夠的朋友,他就會劫持另一個人的慶典。」我比向屋頂,派對和那位瀕死的乙太種的聲音正在樓上歡呼著。「這位失敗者,很遺憾地,我歡迎他留下。」
妖精沒有回應。她的話或許不多,但她的能量竟是如此難以置信地容易讀取。
「那麼。從一到非常想死,妳有多厭惡派對?誠實作答。」
「八。九。與被巴洛西咬掉一條腿差不多。」
我發出了一個不明確的聲音。「那麼糟嗎?」
那雙不可思議的眼睛變得失焦。她想起了什麼東西,並且她周圍的靈氣也帶著一絲苦樂參半的色調。
「在我的故鄉我們也曾舉辦派對。」
我悄悄地斟滿她的酒杯,「那麼妳在那裡做些什麼?」
「我們會交談,重新連結。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徒步前往某些特別的地點。」
「妳是否還經常前往這些地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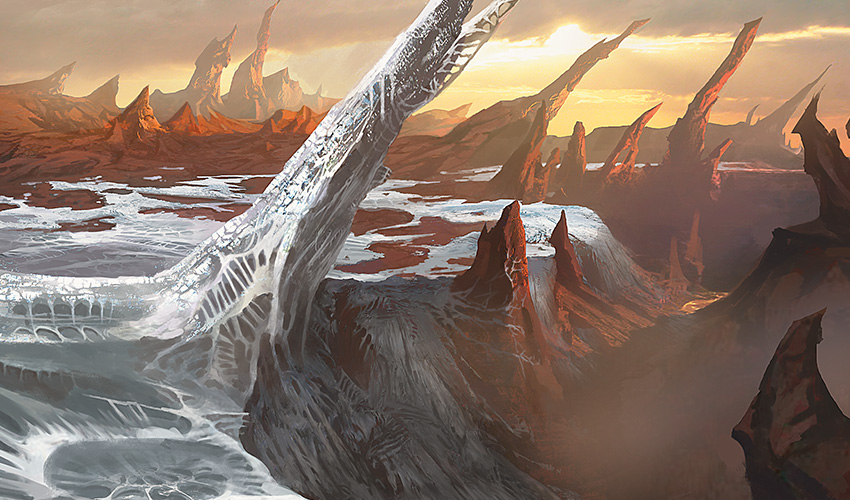
妮莎不發一語。我感覺到那些地方已經不復存在了。「好吧,那麼。我該怎麼做才能讓妳在這場派對中感到更舒適呢?」
「我們可以坐在別的地方嗎?」
「親愛的,我願意為了妳前往這座城市的盡頭。不過是在精神上。而且只有在妳好好地請求我的時候。」妖精被這番話逗樂了。我感覺到她的放鬆,儘管只有一點。她的能量隨著樓上歌曲的變化而改善。多甜美呀。她喜歡音樂。我無視於從我後頸上消散飄起的皮膚。「我們去屋頂吧。妳待在我身邊-觀察周遭的人們可是相當高雅的事呢。」
我感受到妮莎的恐懼並溫和地從人群裡清出一條路來。在往樓上走的過程中,我向一位新來的客人打招呼,並且迅速地把一條手帕遞給另一位臉上殘留著咖哩角碎屑的賓客。派對已自然地來到一段平靜期,而出席者們則愉悅地彼此交談。我將這位妖精帶往位於頂蓬尾端那由策略性擺放的盆栽屏障所劃出的區域。
在我們坐下時,一位隨從靠了過來。我接過他們遞上的精油並在他們的耳邊說道,「派某人調低萬和琴的音量並且保持在緩慢的曲調。」沒有任何財寶能夠比得過一位有求必應的侍者。
「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冒昧,但我覺得妳不像個城市女孩,」我平順地說著。這位妖精淺淺地笑了一下。我往後靠向躺椅,「妳從來沒見過乙太種,對吧?」
「沒錯。告訴我關於你們族人的事,」妮莎溫柔地說道,帶著真誠。在我所積極觀察過的聆聽者中,她是最主動的傾聽者。只不過她的凝視令人感到不自在。
「我們是從乙太循環中產生並具有意識的副產物。我們的家人佔據有年輕人冒出來的地區,然後收養任何一位蹣跚地走出來的人。從第一天起我們就完全成形並且保鮮期就只有四週到四年之間。」
「你描述的內容讓我想起了我遇過的元素生物,」妮莎說道,一邊皺起眉頭。
「那樣的話,妳見過的比我還多。我只知道自己的本質。」
「我不了解。」
「了解什麼?」
她試著做了一個手勢,但我不懂箇中含意。
我覺得有點尷尬。「有什麼事不對勁嗎?」
她又試著比出半個手勢,然後停了一下,思索著她的話。她終於想出一個句子。「我不了解屬於自然之物要如何根源自一座城市。」
「我們就是城市。我是由乙太所構成,而在某一天,我將回歸於其中。自然就在我們四周,它只不過看起來和妳所習慣的樣貌不同罷了。」
妮莎發出一道微小的聲響。顯然她從未以這個方式思考過。
在談話間停頓的時刻裡,我默默地替另一位賓客指點了廁所的方向。
靜默持續著,我看著妮莎閉上眼睛。她在做什麼?她的表情看似感到困惑。傾斜的耳朵彷彿正在聆聽著什麼。難道她聽見了某些我聽不見的聲音嗎?她的嘴角揚起一抹笑容。

「我感覺到了。這個世界具有穩固的架構。循環不已。」
不知何故,這位妖精竟能感應到我的家鄉的本質。
我放鬆地往後靠。「大通聯無所不在,甚至是在吉拉波這裡。我的族人就是證明。我們的荒野並不在乎這座城市是否擁擠,它的節奏依然持續著。」
妮莎的臉上浮現完整的笑容。
我舉起鄰近的一個妖精水壺。「還要嗎?」
「是的,麻煩你,」妮莎不自覺地回應著。我斟滿了她的杯子。或許她不願意透露太多,但我卻可以感受到她因這些驚奇而思緒翻騰。今晚我一定是讓她獲得了滿滿的啟發。
五
我聽見樓下傳來一陣騷動並站起身。妮莎放下杯子並用那雙無邊際的眼睛狐疑地看著我。歲月已經增強了我的感知能力,而且我立刻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發生的地點。
我阻止自己跑下樓梯(耗費體力會讓我更快崩解)並果斷地走向下方樓層的廁所。賓客們分開到兩旁,我才發現妮莎和茜卓現在正跟在我後頭。
在大廳尾端的浴室前方站著一位威風的執政院安全部隊成員。浴室大門很明顯地已被鎖上,而他卻試圖闖入。這位執法者相當高大-幾乎與門邊的盆栽樹一樣高。他的衣服雖然老舊,但摺邊卻是新的;這個男人對肢體衝突並不陌生。在他側邊的武器並不適合用於街道巡邏,但鑰匙與鎧甲碰撞發出的叮噹聲響卻透露了他的職位。他一定是在監獄系統裡工作。
我示意要茜卓和妮莎躲在角落後方,同時我獨自朝那個男人走去。
「我能為您效勞嗎,先生?」
這位執法者鬆開門把並上下打量著我。「有個通緝犯目前正被擋在那扇門後面。無論你的感受為何,他們都得跟我走。」
「所以你進入我的派對-我的房子-但卻沒受到邀請?」
執法者走近了半步並低頭看著我。
「你想讓你的派對違反噪音管制條例嗎?」
「…不…」
「那麼就不要干涉執政院的官方事務。」
我從不懷疑這個執法者會關閉我的派對,只為了要抓到任何躲在那扇門後面的人。執政院就是那樣卑劣。我鄙視卑劣。
我不理會這頭豬玀並前去尋找茜卓與妮莎。對於這件事有個簡單的解法。這兩個人非常結實-她們可以打鬥-而且我也能夠提供她們某些東西作為回報。「如果妳們願意幫我的話,我就提供妳們需要的資訊。」
「你需要什麼?」妮莎柔和地問道。
「妮莎,我需要妳護送這位不速之客離開。」
妖精露出笑容。「樂意之至,」她帶著平靜的信念說道。她舉起一隻手,接著一道溫和的光芒便在那雙無邊際的眼睛裡閃耀著。
我胸口的某個東西開始歌唱了一會兒,但這首歌卻不是獻給我的。我那逐漸甦醒的心靈告訴我要忽略我從遠方感受到的奇異嗡嗡聲響。我轉向茜卓。
「茜卓,我需要妳在他離開的時候打破那扇門。」
琵雅納拉的女兒帶著真實的驚訝看著我。她用一種異常小聲的語調說道,「真的嗎?」
「確實如此。我的身體正逐漸變得衰弱,而且我也無法憑一己之力完成。妳打算這麼做嗎,親愛的?」
茜卓唯一的反應是稍微帶點驚慌,卻又幾乎藏不住的笑聲。聽見一位年輕的人類女子發出那樣的聲音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角落傳來一聲重擊-我彎下身並不由自主地發出一小聲驚呼。門邊的盆栽莫名地纏上了執法者的腿並且那個男人正恍惚地倒在地上。我最好不要去…思考這一切在邏輯上是如何發生的。無論如何,我已沒有時間去在乎了-我在角落轉向並彎身貼近那個男人的臉。
「很好,」我低聲說道。「琵雅納拉。她被關在哪一座監獄?」
執法者發出呻吟。我想他在摔倒的過程中撞斷了一顆牙齒。無所謂-他不需要用言語才能告訴我她的下落。我敞開我的感官並且迅速地說著。
「寇哈里監獄?」
這個男人呻吟著,他的能量散發出憤怒的惡臭。
「古發監牢?」
不耐煩。
「敦德會監獄?」
一份充滿香料與鹽巴的遠憂,卻在他與我四目相接的同時轉變為驚慌。要不是我擁有讀取他能量的能力,我將永遠也無法從他的表情裡猜中答案。他很聽話。我輕拍了一下他的頭。「謝謝你的合作。」
我轉向妖精。「妮莎,如果妳願意的話?」
她走過來並且輕易地以消防員搬運法將這個男人舉過她的肩膀,接著便隨意地把他抬了出去。好吧,可惡。
「這個地方有多少部分是我需要保留的?」茜卓打岔說道,一邊拉下了她的護目鏡。
「理論上全部都要保留,除了這一扇門?」
茜卓點了點頭,露出開懷的笑容,並迅速地以一根放在金屬上的白熱手指熔化了門鎖。我搖了搖頭。人類和他們那些派對伎倆啊。
當茜卓完成時,我感覺到妮莎出現在我背後。因過多精油而導致的惡臭從門與牆壁之間的空間裡滲出。
「任何有肺臟的人趕緊回到派對裡去,」我對旁觀者們如此宣告,使我的注意力轉向賓客。帕西理夫人也在群眾之間,並十分關心地觀望著。我朝她們走去。
「妳們會在敦德會監獄裡找到琵雅,」我低聲說道。
帕西理夫人驚呼了一聲。「不會在那裡吧,」她說道,「請告訴我他說的不是事實。」
我搖了搖頭。帕西理夫人轉向茜卓,「巴羅就駐紮在那裡。」
我周圍的空氣突然開始升溫。「我們現在就得出發了,」茜卓嚴肅地說道。帕西理夫人點了點頭,接著這兩人便走下樓梯準備出發。妮莎逗留了一會兒,雙眼直視著我。
「謝謝你,耶赫尼,為了這場談話。」
我點頭致意。「不客氣,親愛的。如果一個月後妳有空的話,妳應該回來。我將會舉辦一場此生最大型的派對。就連妳也不想錯過呢。」
她面露微笑,不一會兒她就離開了。
六
我打開那扇現已解鎖的門,迎面而來的是一波香水的惡臭。門在我後方關上,接著我轉身查看是誰把他們自己鎖在這裡面。稍早時我感應到被困在籠裡的悲痛,而足以確定的是,那個來源正坐在這裡。在浴室尾端,背倚著牆坐在地上的,正是稍早時那位垂死的乙太種。他們的皮膚幾乎已完全消失,而他們那發出藍色光芒的精華正與透過窗戶灑進來的夕陽怪異地交融著。許多空的香水瓶四散在他們腳邊。

「把好東西都留給你自己一個人獨享呀,」我一派輕鬆地說出安慰的話。我格外意識到我的妙語就像是一塊絲綢覆蓋於一道敞開的血腥傷口上。
「我差不多只剩一分鐘了,」他們氣喘吁吁地說道,「我被執政院跟蹤而且我不想在眾人面前現身。」
「你從監獄或某個地方逃脫嗎?」我問道,我在他們腳上瞥見一條破損的腳鐐。這位乙太種就只是呻吟著。
我坐在他身旁。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話也會想要有人陪伴。「樓上有任何人知道你的名字嗎?」我問道。
「沒有。他們只是來這裡參加派對的。」
「那就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出現在這裡的原因呀,親愛的。」
我吸了一口在空氣中徘徊的香水味。隨著其他乙太種持續消散,他們的能量也與濺灑出的精油混雜在一起。我曾見過許多族人垂死的時刻,並且幾乎總是帶有某種勝利的神態。他們在生命的榮光之中打鬥、踢踹、搔抓、作樂,而在此他們已抵達了終點線。
我握住了他們的手僅存的部份。
我能夠感覺到他們的能量在我的掌心之下搏動著。
「你有個精采的人生嗎?」
另一位乙太種把頭轉向我並仔細地看著我。他們使勁地想說話但卻只擠出了一句肯定。「我還真的做到了。」
在那一刻我好羨慕。我只剩這麼一點時間。我的人生,這樣的乙太種人生,我所有族人的人生都在這少的可憐的時間裡儘可能地追逐並累積更多經驗。我們得如此迅速地燃燒還真不公平。
下一個就輪到我了,真不公平啊。
另一位乙太種開始抽搐並吐出一道黑煙。他們的皮膚崩解,而內含的乙太則逸散並化為蒸汽飄升至天花板。
我靜靜地坐在那團迷濛的乙太下方。它好美。
過了片刻,我起身打開窗戶。那股臭味與能量便飄散到空氣中,進入這個世界,融入了通聯。我轉向遺留在地上的一疊衣物,並將衣服與他們的珠寶和配件收集在一起。一個零錢包,一個時鐘,一捆執政院的文件。我迅速地翻看了一下-只是輕微的竊盜小罪。他們一開始就不該被送去監獄。
我憤怒地把文件揉成一團。那些執政院混蛋們正在加速我們的死亡。
當我在整理這個陌生人的珠寶並戴上其中一條手鍊時,我心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念頭。
要是我離開這個派對並走出去的話呢?要是我獵捕那些拘留這位乙太種的執政院穢物並讓他們遭受應得的懲罰呢?我之前曾經吸取精華過(一次,純屬意外);那種感覺真美好。我可以再次這麼做。我可以再這麼做一百次,如果有人活該的話。
我看著一縷輕煙從我的皮膚升起飄向敞開的窗戶。
我想著那位被丟在我家外面的大街上卻又不省人事的執政院執法者。
他還會在那裡待上幾個小時。
我可以偷溜出去幾分鐘。
沒有人會注意到的。
不。還不是時候。當輪到我坐在浴室地板上,被空香水瓶環繞並且從我的縫隙裡不停噴發著蒸汽時…或許到時候我就會這麼做。
我剩餘的時間要用來做其他的事。
我拿起其中一瓶半空的乙太精油並將它灑在自己身上。生動又堅毅的安卓雪松。能量竄流過我全身,新借來的黃金在我的脖子上不停閃耀,而派對的喧囂正從屋頂上迴盪而來。
我衝上樓梯,現身於剛落下的夕陽以及位於絲金底座上的眾多燈籠光芒中。群眾分站兩側,敬重我在由我所創造的生態系統中的權力,而萬和琴也停止演奏。我堅定地走向主要頂蓬,刻意地舉起了雙手。我的賓客們噤聲不語並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我。
我大喊著,「尊貴的賓客以及平庸的地痞,在你們的日曆上記下從現在起一個月後的日子!」
我的朋友與賓客開始歡呼。他們就跟我一樣。他們享受他們的高檔身份與低階門檻。
「我即將於發明家博覽會結束後在此舉辦一場今生千載難逢的派對。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在這裡,並且告訴每一個你認識的人如果錯過的話他們就是笨蛋。」
他們歡呼。我覺得自己彷彿可以再活個十年。
「不過,說夠了。你們都不想再聽到關於我的事了,對吧?」
派對嘶吼著,「我們當然想啊!」
「好吧真可惜!我已經講到煩了!回到舞池去,把音樂調大,並且來個誰替這裡每一個擁有肝臟的人再開一桶酒吧!」
群眾失去理智。尋歡作樂的集體興奮感激湧過我全身,我已迷失在它的潮流裡。我衝進正在跳舞的人群,同時闖入了某人灑向空中的一團乙太精油中。音樂增強,歌曲的節奏正驅使著我周遭的身體移動並且一切都令人感到生意盎然。乙太種散發的微光反射了舞池群眾的汗水,柔和的乙太捲鬚消散於上方的天空中,而且我還活著我還活著我還活著,並且這一刻我正沉浸於存在的狂歡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