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斯編年史:熟悉的陌生人
在平坦的凍原通往黑山的西側山脊之處,山丘突出於地表上,宛如一條自堅硬地面竄出的巨龍那參差不齊的牙齒。在山丘之間矗立著一座扭曲成巨型螺旋的石塔。在它旁邊,一陣詭異的藍綠色光芒宛如薄霧般地自一道劈開大地的裂隙中飄出。
這裡,位於通往烏金之墓的入口,祖母抬起手而非出聲示意他們的隊伍停下。深邃的裂隙創造出一座割穿冰霜與岩石的廣大峽谷。倒在峽谷底部的物體被隱藏在一個由尖銳岩石構成的巨繭中,上面灑著白雪並飾有不停裂響的冰晶紋路,描繪出了交織於岩石表面那高深莫測的符文。
從他們站立之處俯視,並沒有路可以進入這個峽谷,儘管與裂谷相鄰的岩石地面一直遮擋住他們看見那條覆塵小徑的視線。奈瓦記得在六年前前往烏金之墓的旅程,跋涉穿越凍原,誘捕鳥兒並且追獵一群羚羊,以及他們抵達這道裂隙的方法。後來她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們以奇特的隊形走在狹窄的小徑上,並沿著峽谷的邊緣走向一座淺穴。他們在那裡紮營了十個夜晚。
祖母以雷鳥的粗啞叫聲呼喚,然後側耳傾聽。
在他們等待回應的同時,奈瓦緊張地移動著。這道光芒讓她感到不安,就跟沿著裂隙深處蔓延的石繭一樣。這些東西是否長得比它們六年前更龐大了呢?那些神祕的符文變多了嗎?
「那些是什麼?」泰靖低語著。
「祖母稱它們為晶石。它們能保護靈龍的遺骨。」
「啊。那我們在等什麼?」
「前方有個洞穴。不時會有狩獵隊伍紮營在那裡。」
「為什麼?」
「在這裡狩獵特別好,因為龍族不會靠近這個區域。而且我們得抵禦歐祝泰族和寇安甘族的進犯。如果他們有本事的話,他們也會來這裡狩獵,從我們的領土上竊取獵物。」
「我的意思是,為什麼我們在等待而非繼續前進?」
「為了讓他們知道我們來了。我們不想要驚動他們。」
泰靖低頭注視著裂隙與晶石那閃閃發光的表面。它們不透明;難以看見是否有骨頭在它們下方,就像祖母所宣稱的。彎曲的峽谷山壁遮擋了其餘的石繭。
「我沒想到靈龍竟是如此龐大,」泰靖低語。「我以為他和龍王們一樣大小。」
「不,他是龍族中最偉大的,當然他必定如此,因為他是整個韃契的始祖,」百夏插嘴。她站在泰靖的另一側,在研究晶石的同時一邊用手遮擋眼睛,臉上還掛著神祕的淺笑。
有個念頭戳刺著奈瓦的頭:奈瓦才是先對這位年輕的靈火戰士感興趣的人,而百夏這樣炫耀她的學識還真惱人呀。她的雙胞姊妹早已擁有較多來自祖母的關注。難道她不能留給奈瓦一點什麼嗎?
一道刺耳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緒:祖母吹出了更大聲的哨音。
只有風回應著。
「梅芙菈是上一季來到這裡的團隊首領。即使他們外出狩獵,他們通常會留幾個人待在營地進行燻製獸皮之類的工作。」祖母朝費克做了個手勢。「你攀上小徑前往洞穴。馬塔克,你、歐弋陽、拉坎,以及索爾婭待在這裡看守泰靖。」
「妳認為這一直都是歐祝泰的詭計嗎?」馬塔克提問,一邊怒視著泰靖。
祖母那嚴峻的目光停留在這個年輕人身上。「那或許是。我要你們保護泰靖不受任何被派來跟蹤並殺害他的歐祝泰族同胞襲擊。躲在岩石間。女孩們,跟我走。」
費克迅速地消失在小徑的彎道裡,而其他人則藏身於岩石陣中,也就是那些當靈龍撞上地面時自峽谷濺起的碎片。
「怎麼了?」奈瓦問道。「妳覺得他們去哪裡了?」
祖母觸碰嘴唇示意安靜。她帶著女孩們原路折返穿越碎石原,抄近路走過零星分布的倖存樹叢。在約莫兩百步後,她讓她們看見刻在一株古杜松樹幹上的凹痕。在樹叢之間側身滑動,她們輕鬆地通過這片樹葉並現身在一條乾涸的河床上。她們沿著河床往下走了一小段路,在光滑的石頭上滑行。祖母停在一顆巨大的岩石旁,半隱藏在一種被稱作哭泣漿果的藥用植物的濃密枝幹中。岩石上刻著一個記號:「鐵木爾之爪」,現已被安塔卡禁止。她撥開垂掛的枝幹,露出了通往一條隧道的狹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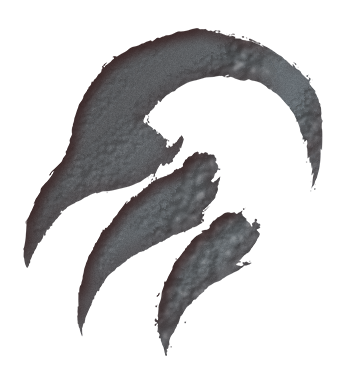
她先點了一下奈瓦的鼻子,然後是百夏的,當她們還是幼童的時候,這是個用來引起她們注意的老手勢。「這份知識屬於低語者,還有長老們。絕對不可告訴其他人。妳們懂嗎?」
「懂,」百夏說。
奈瓦皺眉,因這些嚴肅的話語而感到既困惑又興奮。「我了解。」
她們排成一列行進,祖母走在前頭,奈瓦殿後。過了一會兒,通道轉了一個大彎並且她們出現在一個約有一百步寬的袋型谷中。谷內的空氣相當溫暖,幾乎是溫和宜人的程度。泉水周圍長滿了可食用的植物。上方的天空因包覆的岩壁而變得狹小,但活物的濃郁氣味卻讓這座微小聖殿顯得豐饒富足。
百夏跪在泉水旁。「這好美麗。看,這裡有野櫻梅、碎石草以及微光苔蘚。怎麼會這麼像夏天?」
「這是一個聖所,祭師們會來這裡冥想。現在更不只這樣,是個躲避龍族的聖殿。」
「它怎麼能夠躲避龍族?」奈瓦問道,一邊指著天空。
「一種交織於岩石裡的魔法從上方將它隱藏。不過這種魔法只能涵蓋一小段距離而且每年都需要更新。」
「為什麼妳要帶我們來這裡,祖母?」百夏問道。「我們可以在費克進行偵查時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祖母緩緩地轉了一個圈,一邊仔細觀察這座小型峽谷,彷彿要確保一切都跟她當初離開時一樣。「如果事態變糟,或是我最糟的恐懼成真,妳們可能就需要在這裡避難。」
「什麼恐懼?」奈瓦問。
「撿起一顆石頭。」
四堆整齊的拋光瑪瑙標記了四個方向。這些石頭散發的熱能溫暖了空氣。當奈瓦拾起一顆時,她發現被她誤以為是拋光光澤的竟是一道溫暖的光暈。百夏倒抽一口氣,欣喜又驚奇地睜大了眼睛,而且她也拾起了一顆石頭,把它靠在臉頰上,然後微笑著將它捧在手心。
祖母用兩根手指觸碰嘴唇要她們安靜,接著便比向位於山谷遠處的一個隧道入口。她們靜靜地跟在後方,輕柔地在石地上拖著腳步行進,彷彿正要進入大地的骨架裡。岩石包圍了她們,保護著她們;來自這顆石頭的光芒點亮了她們的路途。隧道的牆上畫著野牛與羚羊,熊與狼,叉角鹿與麋鹿的輪廓。狩獵隊伍圍繞著年輕的龍,用網子固定住牠們,同時將長矛轉向脆弱的腹部與眼睛。在這些優美的圖畫之間刻著鐵木爾之爪以及其他奈瓦從未見過的印記-螺旋與火焰,蛛網與布滿裂隙的冰雪山巔。在其他情況下,像她這樣的人將永遠無法看見這個神祕之地。不過她是一位祭師的雙胞姊妹,而且祖母做任何事都有其道理。
終於,隧道擴張為一座長型洞穴,它的牆面如此高聳,連石頭的光芒都無法穿透上層的黑暗。陰影宛如靜靜等候她們歸返的親族般地迎接她們。隨著她們走近,這些圓形的陰影便逐漸顯化為置放於石柱上的大型頭飾。這頂特大號的皮製兜帽上串著雕骨、鹿角、獠牙,以及由青銅鑄打成的護符。
百夏突然停下腳步,使奈瓦撞上了她。「祖母,這些是什麼?」
「它們是低語者的服裝,正如妳註定成為的身分。我們把他們藏在這裡以躲避安塔卡。妳無法再向安塔卡隱瞞身分的那一天將會是妳加入隱匿者的日子,我的孩子。我們得把妳藏起來不讓她發現。」
「藏在一座石墓裡,就跟我們的母親一樣嗎?」奈瓦質問。
「噓,別這麼大聲,我勇敢的獵人。妳原本能夠慢慢了解這一切,但現在已經沒時間了。仔細聽好,奈瓦,因為這有一部分也跟妳有關。妳擁有成為一個偉大獵人的技巧,以支撐我們的族人。但妳卻有機會做出甚至比那更重要的事。」
「有什麼比餵養部落以及餵飽安塔卡以免她殺了我們還重要?」奈瓦問道。
「什麼是更重要的?就是保存關於我們真實自我的知識。」祖母從她們身邊經過。架子被直接雕刻在石頭中。在這裡,一批獸角、獠牙,與鹿角一字排開。石頭的光芒照亮了位於它們表面的雕刻,這些精緻、繁複的紋路顯然出自雕刻大師之手。這道光芒也照出了祖母的表情軟化為罕見的滿意神色。在他們嚴峻的生活中很少有東西能夠緩和她的戒心,不過當她拾起其中一支鹿角並在光暈下將它傾斜以仔細端詳其上的雕刻時,她確實露出了笑容。
「這些雕刻講述了過往的故事。只要我們的先祖活在我們的記憶中,那麼有朝一日我們便能夠找回我們自己,而非只侍奉安塔卡與她後裔的飢餓。」
「有關於戰鬥和屠龍的故事嗎?」
「有的,而且還不只那樣。妳們早該成為這份知識的守護者了,好讓妳們能夠在我走了以後把它傳承下去。」
奈瓦從祖母手上接過這支鹿角並檢視刻在骨頭上的雕紋。沒有屠龍,而是屠龍的人類。她突然明白了這是可汗衰亡的故事,一則祖母經常在晚上的壁爐邊講述的故事,同時作為警告與提醒。
百夏甚至沒有靠過來看這件骨雕。她往回走向那些頭飾,把手伸向最靠近她的一個,接著又驚恐地把手縮回。在不平穩地吸了幾口氣以回復鎮定後,她再次伸手,而且這次她用手指沿著這些象徵力量的物品輕掠而過。她的臉上浮現敬畏的表情。
「我聽見你了,」她低語著。
當然,這些物品正在向她低語著秘密。這項傳統屬於那些擁有祭師天賦的人;它並不屬於像奈瓦這樣的獵人。她只是因為百夏才會在這裡。
這好不公平。
祖母拿起鹿角並把它放回去。「費克應該已經抵達營地了。跟我來吧。別出聲。不要帶光。」
她們將石頭放回地上並跟著她進入一條寬廣的隧道,也是唯一的另一個出口。天花板逐漸往下傾斜,一直到她們只能匍匐前進的程度。費克那深沉的聲音在她們四周低語著,儘管聽不清他的話語。他稍作停頓,彷彿正在聆聽,接著再次說話,顯然正在回應。為什麼祖母要暗中監視而不是像平常一樣迎接她的親族?

通道的尾端是一道眺望著那座巨大淺穴的狹長水平裂隙,因太過狹窄而無法鑽出。石壁爐上蓋了一層精細的白灰。部落獵人的包裹和武器四散於石牆後方的地面上,它的高度足以擋下遊盪的野獸,但獵人們卻不見蹤影。費克背著陽光站在入口處。他正看著某個位於洞穴後方的人,他們的臉孔與形體在陰影下朦朧不清。
祖母從齒間發出輕柔的嘶聲。
一道低頻的聲音從陰影裡傳出,語調既甜美又憂鬱。「一場疾病吞噬了他們的生命,為他們帶來死亡。只剩下我一個。」
「妳是誰,女族人?出來讓我看清妳的臉。」
「我不敢迎接你,兄弟,以免傳佈那害死其他人的疾病。」
「妳病了?」
「我沒有。但或許這個疾病藏在我體內。死亡有許多種偽裝並且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出擊,不是嗎?」
費克把一隻手藏在背後,然後比出了「小心」的手勢-這表示他知道這道隱密的裂隙並且假設祖母早已抵達那裡,正在觀察著。「他們是多久以前死的?」
「我算不清日子了。夢境在夜晚煩擾我。你知道任何夢嗎?」
「我不做夢。」他伸出雙手顯示自己未帶武器。「正如我說過的,我叫費克,屬於阿貝克族裔,現在是第一族母婭紹娃的養子。我再問一次,我可以知道妳和妳的家族嗎,小妹?」
寂靜填滿了空氣,宛如從火裡散發的熱氣。這個人影從洞穴後方的黑暗中往外走了一步,顯化為一個拿著斧頭且大腹便便的女子。頭髮上罩著一頂毛帽。陰影斑駁了她的臉孔,使人難以看清她的五官。
「第一族母婭紹娃,」她以那種如蜂蜜般甜美的語調說道。「我知道這個名字,但我不認識你,阿貝克族裔的費克。帶婭紹娃來見我,我就會跟她交談並告訴她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她將會知道那些夢境。」
「妳還需要什麼嗎,小妹?在我回來以前是否有任何妳需要的東西?」
「我已經有了所需的一切。」她把一隻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好像在提醒人們每一個出生的孩子都將走上部落的正道,聯繫著過去以及尚未實現的傳言。
「這是妳的第一個嗎?」
「我的第一個?」
「妳的第一個孩子。妳看起來即將臨盆,而且這裡沒有任何助產士或治療師。」
「是的,對,一切都好。時間快到了。婭紹娃在哪裡?」
他張開手拍打胸口彷彿認可她說的話,但這其實是一份給祖母的信號,表示他們將會與其他人會合。「我會看看我能做些什麼,小妹。不過這可能會花點時間。在這裡靜候我歸來。」
她不發一語,就只是等著。他頭也不回地離去,最後消失在日光中。直到此刻她才返回陰影裡。一股黑暗包圍了她,只留下一雙閃爍的眼睛。
奈瓦默默地與祖母和百夏一起往後爬行,直到她們抵達那座擺放著頭飾的洞穴,那些物品宛如等待被釋放的幽靈。
祖母遞給每個女孩一顆石頭。她的面色凝重。
「我的女孩們,妳們對我來說是最珍貴的。」
聽見她大聲地說出這些話使奈瓦喘不過氣來。有那麼一刻,她以為密室裡的所有空氣都被吸出而且她即將窒息。總是感應到她雙胞姊妹的情緒,百夏抓住她的手並捏了一下。
「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我們之中記得過往時代的人正在走向先祖的寒冰,而那些即將出生的人將永遠無法得知我們曾經的過去,除了透過別人講述的故事,而這些人也從未見證過自已講述的內容。妳們是我鍾愛的女兒所僅存的一切。但現在妳們也是我獻給傳言的供品,妳們和我們製造的雕刻品將會講述我們的故事,好讓其他人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聽過我們。」
「發生什麼事了?」奈瓦質問。「妳認為那個女子的病會傳染給我們嗎?」
「難道妳沒認出她嗎?」
「沒有。」
百夏說,「很難看清她的臉,不過我覺得她看起來像梅芙菈。」
「對,那個身形很像梅芙菈,但我相信說話的人不是她。」
「妳是說有人竊取了梅芙菈的外貌嗎?怎麼可能有人辦到?」奈瓦問道。
「我的療癒魔法十分強大。世界上還有各式各樣強大的魔法。」
「就像百夏移動石頭和冰塊的方法。」
「沒錯。或許魔法能夠把一個人塑造成不同的形體。或許它只不過是藉由幻影來讓我們相信某個不存在的東西。我不知道。但費克擁有絕佳的嗅覺,透過他的手勢,他也懷疑那不是她。我需要更靠近並且親自詢問這個人才能夠確定。在我這麼做的同時,我要把妳們兩個留在這裡。」
「我不怕,」奈瓦堅決地說。
「妳當然不怕。」祖母緊緊握住每個女孩的一隻手。「但在我弄明白烏金為何要傳送幻視給我們,或者它們是否真為烏金的幻視之前,妳們兩個都必須待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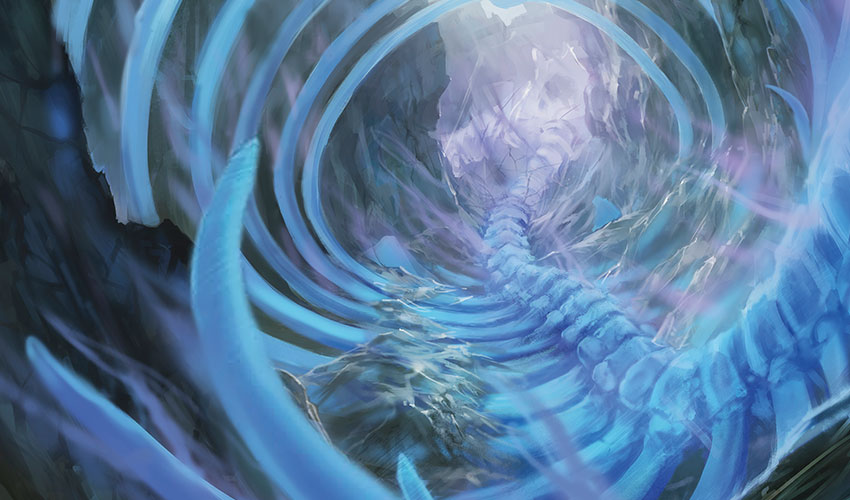
「不然它們會是誰的幻視?」
「一個早就污染我們的闖入者,造就了龍王的霸權。如果我和其他人出了什麼事,就等一個月。」
「一個月!」
「照我說的做。一個月後,返回阿亞戈並告訴哲拉克他現在是部落的第一族父。」
沒再多做解釋,她便離開了她們。
「什麼闖入者?」奈瓦凝視著祖母離去後的漆黑空間。「一個闖入者怎麼能夠造就龍王的霸權?難道龍族不是註定要統治我們的嗎?」
「一條繩索並不只是單一的絲線,而是由許多絲線交織在一起,」百夏輕柔地說。「未來就像是那條繩索。我們現在身處的絲線並不是原本唯一的一條絲線。曾經有不同的道路,一條沒有被選擇的道路。」
「妳現在聽起來真像個低語者!」
「我是個低語者。難道妳不記得那個故事了嗎,奈?那天的風暴裡有另一隻巨龍,殺了烏金的那隻。他憑空出現又憑空消失。」
「難道祖母認為他回來了?」奈瓦環抱雙臂。這裡突然變得好冷。「她不能獨自面對一條龍。我們應該返回那座高地然後看…」
「不行!」百夏平常溫和、遲疑的語調突然變得強硬,使她聽起來像另一個人,不是奈瓦在某些方面非常熟悉,但心靈卻又與她大相逕庭並時常困惑著她的那個害羞、夢幻的雙胞姊妹。「我們不能回到那裡去,奈。我知道我們應該去哪裡。」
她拉著奈瓦走進洞穴最陰暗的角落。石頭的光芒照出了一道非常狹窄的裂隙,但百夏早已卸下她的背包只為了要擠過這條縫隙。
「妳在做什麼,百?祖母要我們待在這裡。」
「烏金正在呼喚我。我之前從沒聽見過。或許是因為我們太過遙遠,它只能透過交織在頭飾裡的魔法聯繫我。」
「烏金已經死了。死了的東西就是死了。」
「不。死亡比那樣更複雜。如果妳不想來,我就要自己去了。」
當她出發攀登恆冰山時也說了一樣的話。一部分的奈瓦想要阻撓,想轉身離去。但就在百夏動身登上聖山的那天,奈瓦知道她的雙胞姊妹已決心走上這條路而且永不回頭。既然保護百夏是她的職責,她便放下背包,並且依然握著那顆石頭,跟著她側身鑽入縫隙。她的鼻子摩擦著岩石,同時側步前進。她的後腦一直撞上另一側的岩壁。在側行了一百一十步後裂隙變寬,使她能夠和她的雙胞姊妹併行。百氣喘吁吁,稍微咳了幾聲。
奈瓦將一隻手臂搭在她的肩上。「妳看,前面有一道日光。我們可以把石頭放在這裡好讓我們在回程的時候使用。」
裂隙通往一座淺穴,那裡的石頭排成一圈形成一個火坑。已經很久沒有人使用它,所有的灰燼都已消散,而且奈瓦也沒看見任何囤積燃料的跡象。她們發現一條小徑,沿著陡峭的峽谷表面來回折返而下。太陽還沒到天頂,但峽谷內卻一片陰暗,於是她們便小心翼翼地踩著腳步。這條小徑差不多是一隻手長的寬度。很容易就會翻落到冰封的晶石尖棘上。風聲隨著她們往下走而消逝,一片濃密的死寂淹沒了她們,彷彿她們的耳朵塞滿了布。一股深沉、安靜的震動以一種緩慢的節奏透過她們的靴跟傳遞上來,這讓奈瓦想起了呼吸,但這下面除了這兩個女孩以外並沒有任何活物。連飛鳥也沒有。當她舔舐嘴唇時,空氣幾乎要在她的舌頭上燃起火花,就好像她們正走進一片隱形的冰凍閃電裡。
小徑終於來到谷底,前方是一條死路。歪斜的晶石牆困住了她們。無路可走,除非往小徑折返。
她的雙胞姊妹總是把她帶往一條死路。這個念頭悄悄爬進奈瓦心中。她總是得跟著祖母為百夏規劃的路線前進,而非掌控因她的狩獵才華而授予她的榮耀。她應該得到更多。
「奈?」
「怎麼了?」感到驚慌,奈瓦轉身看見百夏正瞇起眼睛看著她。
「剛剛妳的眼睛有點奇怪,不過那已經消失了。妳看我發現了什麼。」她用手指著其中一顆晶石的下方角落。宛如一片鬆脫的龍鱗,她搬動一塊板狀岩石,露出了一個足以匍匐穿過的洞口。
「不要進去裡面!」
百夏跪了下來並爬進去。她的腳消失了。大地嗡嗡作響,然後又恢復平靜。
奈瓦對自己的勇氣相當自豪。看見缺口裡頭一團漆黑,沒有光線能夠穿透,這讓她心裡產生一絲恐懼。懦夫!她一輩子都被不斷提醒著要保護她的雙胞姊妹。她總是認為那是因為百夏比較虛弱、脆弱、能力不足,或許會被部落判定為一個不值得餵養的人。但根本就不是這樣。
祖母愛她勝過愛妳。妳可以丟下她。沒有人會想念她,然後祖母將會更愛妳。
這個念頭不斷煩擾她。她朝小徑的方向往後退了一步。又一步。
妳有更偉大的命運。妳將成為族人間最偉大的獵人。一旦不再有她成為妳的負擔,那將會很容易。
但責任與愛卻使她停下腳步。不可能就這樣一走了之並把她的雙胞姊妹拋下。她們一同出生,從她們死去的母親那血淋淋的子宮裡被拉出來,緊握著彼此的手。背叛那份連結就是背叛她自己。
於是她跪了下來彎身進入晶石。
她眼前飄著一片閃耀的迷霧,模糊了她的視野。色彩宛如絲線般扭曲,不停閃爍,令人目眩神迷。空間廣闊,難以估算,使人陶醉的永恆氣息甜蜜地拂過她的臉。同時,這個空間就跟在隆冬時節抵擋冰雪而架設的獸皮帳棚一樣小,狹窄又潮溼。百夏平躺在地面上彷彿在睡覺,一隻手無力地垂在一側,而另一隻手則伸過她的頭抓著一樣奈瓦看不見的物體。
奈瓦肺部的空氣為之凝結。她往前傾倒,同時視野也變得模糊。用她清醒的最後一口氣,她緊握住雙胞姊妹的手,肌膚相觸。晶石的魔法在兩個心靈之間開啟了一道門。靈龍的精華宛如冰崖般地在她周圍升起,輝煌閃爍且無法穿透。她墜入百夏早已深陷的幻視中。

這座地貌是一片銀白色的水,就跟一面往四面八方延伸的鏡子一樣平坦反光。不時有零星的岩石島嶼如尖塔般地自無垠的海中升起,每個都構成了可供冥想的完美歇息處所。
空氣中平靜無風,不過卻有許多閃爍的半透明光球飄浮著,宛如在微風中的泡泡,什麼也沒觸碰到。
其中一顆光球飄近,而且離沉眠於水面上方的女孩的夢影更近。當它那脆弱的表面觸碰到她朦朧形體的邊緣時,它啪一聲地破裂了。稀薄的水珠將記憶濺灑入她心靈的陰影中。
一條龍盤旋於靜止的水面上,凝視著牠的倒影,像是一面回望著牠自己的鏡子。倒影的每個細節都如此完整,可能是原本的龍正在看著一片鏡像海,而飄浮於上方的龍或許才是牠的倒影,每個細節都十分完整。
「這是什麼地方?」這條龍說,並且在聽見自己的聲音時驚訝地揮打尾巴。但揮舞的尾巴卻沒有激起任何風。水面沒有漣漪。只有倒影隨著巨龍的自問自答而移動。
「這一定是忒祝祈提過的其中一個時空。我已經穿越了世界之間
這份領悟燃起了一股不停閃爍、無光的火焰,看似包圍了這條龍,而且牠就這樣消失了。
水面一動也不動、平靜地等待著,卻又滿懷期待,幾乎有所感知。另一顆光球旋繞著升起飄向那位沉眠女孩的陰影,然後啪一聲地破裂。
這條龍困惑地下墜,在最後一刻張開翅膀懸浮在一座崎嶇的山巔上。不過這並不是牠那座擁有平滑斜坡的誕生山區,號令著一片壯麗、豐饒的地貌。這是一個狂野、充滿風暴,才半成形的崎嶇世界,名為韃契。狂風以蠻野的呼嘯迎接這條龍。山脈在歌唱,噴出了熾熱熔岩的樂曲,而河流則在欣喜的歡聲中激湧而出。這條龍的內心體會到家的感動。牠能夠照料這片荒野,並非為了創造牠欲求的花園,而是要成為它自己,以實現它那新生靈魂的允諾。
於是,他探入土壤並掘出了大地的生物。他在翻騰的河水和激盪的海洋與黏重的泥沼中悠游,每一個氣泡波紋都為水域增添了數不盡的生物。他的翅膀拍擊帶來雷鳴與裂空閃電,而這座風暴則孕育了龍族。甚至連火也造就了活物,在它們的熱度與美麗中輝煌閃耀。
至少,這是人形生物在編造關於遠古時代的傳說時經常講述的一則故事,因為那些見證過龍族的壯麗與力量的人都忍不住希望能與牠的輝煌扯上關係。隨著魔法的知識在不同民族之間興起,祭師們開始尋求龍族的教導。他向最聰明的人講述他來到韃契的故事。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他發現當時強烈的震驚與背叛感已逐漸消逝。他的雙胞兄弟發生了什麼事?尼可活下來了嗎?他們誕生的時空狀況如何?如果他能夠穿越時空一次,他肯定能夠再穿越一次。
他在心中尋找那盞打開跨世界通道的火花。在一陣無形且不停起伏的火焰中,他穿過一片漆黑、混亂的黑暗並且,在一股反胃的不適感過後,發現自己再次飄浮於靜止的水面以及它們那冥想靜心的神祕 氛圍上方。

他凝視著正回望著他的完美倒影。
從閃爍的天空中落下一滴水,又或許是從他眼中落下的,擊中了水面。它的漣漪開啟了一幅景象。透過這扇窗,他看見誕生的山區,依然高聳,依然覆著白雪,但現在卻被難看的生長物破壞了。
就像一道無聲的痛苦咆哮,所有他以為早已拋下的濃郁、凝結的情緒再次激烈地湧現。火花賜給他通行權;他扭身穿過暗影,然後他就到了那裡,從空中墜向那座誕生的山區。
他乘著一股強勁的氣流升起並繞著山脈行進,逐漸盤旋下降直到他看見某個人在山頂建了一座殿堂。這棟建築是個華麗的奇景,擁有漆成如血液般鮮紅的多層屋頂,頂端還有一雙朝彼此彎曲的巨角。身穿長袍的僧侶朝他跑來,看見了他,接著便鳴鐘擊鼓。有些人宛如敬拜般地俯伏於地,而其他人則朝他拋擲如網子般的魔法打算捕捉並把他拉下來。
他躲過這些粗糙的魔法並沿著山脈往下飛,一邊尋找任何熟悉的事物。這片空地是梅瑞婭薩爾被殺害之處,也是老族長建造殿堂的位置,現在卻是一座大城的中央廣場。這座大城沿著山脈延伸,一路來到古老聚落曾經佇立之處。
有太多人形生物在這座城市的街上走動,他數不清人數。他們的聲音就跟無邊的河水一樣湍急,但在這片熙攘喧鬧之下卻潛藏著一種靜止不變的腐壞。一種潰爛的黑暗覆蓋了小巷與房屋並且滲入每一筆交易中。在那些戴著繡有彎角徽章的富人,在大桌上用餐並在豪華殿堂裡任職的人,以及帶著鐵劍與長矛誇耀他們的豐功偉業的人之下,匍匐著被束縛與挨餓的人,還有奴隸與被冷落的人。基本上,這個地方看起來與那位屠龍族長的古老浴血聚落有點不同,就只是擴張並轉移了。
現在這裡由誰統治?
但他心裡明白是誰在統治這裡。
他認出了那雙彎曲的角。
我的兄弟。我的雙胞兄弟。
他還是背叛了我,背叛我們許下的承諾,背叛我們共享的連結。
發出一聲沮喪、憤怒、哀傷的嚎吼,他消失在一陣無形的火焰漣漪中。在極為不適地穿過黑暗虛空後,他再次現身於夢幻的鏡面上方。
平靜的水面平撫了他煩擾的心。可惡的情緒衝擊得到舒解。經過了無數年,他盤旋在水面上,迷失在思緒以及自我的目的中。他第一次墜落地表的世界─多明納里亞─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當有一整個宇宙的世界在等著你探索時,為何還要煩惱過去?他並不受限於誕生的山區或甚至韃契,他靈魂的家園。宇宙比他偉大,本來就應該如此。他心中浮現一股新的平靜。帶著歡欣、喜樂、目的、安寧,他躍入一陣無形火焰的漣漪中。
這條龍消失了。
水面一動也不動、平靜地等待著,卻又滿懷期待,幾乎有所感知。另一顆光球旋繞著升起飄向那位沉眠女孩的陰影,然後啪一聲地破裂。
他穿越眾多時空,奇觀與危險也隨著他在不同時空之間穿梭而展現。動盪的贊迪卡。月亮護持的依尼翠。陽光普照的洛溫。健全且魔法力完美平衡的阿拉若。魔法豐饒的山德拉。還有好多,有些遼闊又富含魔法力,有些弱化的斷片則同時流失了生命力與魔法。

忒祝祈是否曾懷疑過宇宙有多少樣貌?多重宇宙的壯麗使他感到敬畏;它的廣大讓他感到謙卑。
不過他卻一直想起他的雙胞兄弟。這段時間他一直迴避多明納里亞,在他過去的桎梏裡感到被困住並且削弱。或許是他太快懷疑尼可,他畢竟只是個非常年輕的龍,並且正如青春的本質,容易因衝動而犯錯。或許他誤會了那對彎角的意義。
他的自尊心也很強,就像他的雙胞兄弟,難以忘懷過去的傷害。或許他只看見他想看的,卻沒有完整探索以發掘真相。的確,真相比自尊更重要,比力量更令人滿足。
他會找到尼可,而且他們將會回到從前的狀態。他很肯定。
到目前為止,他已精通於穿梭時空。在一眨眼間,伴隨著一陣無形火焰的漣漪,他離開了。
水面一動也不動、平靜地等待著,卻又滿懷期待,幾乎有所感知。另一顆光球旋繞著升起飄向那位沉眠女孩的陰影,然後啪一聲地破裂。
旗幟在風中飄蕩,軍隊穿越了杰姆拉的平原。在他們後方散佈著一場大戰的殘跡:破碎的屍體,傾頹的城市,以及被毒害的大地,肇因於由無情巫術與龍族蠻力所引導的戰爭。散落於各處,標記著阿卡迪薩巴斯皇冠的旗幟被折毀於泥濘中,而部屬們則被一群追趕的軍隊擊敗。繪有那雙彎角的軍旗持續推進,直到那些逃竄軍隊的自豪倖存者們聚集在一起,準備好面對一場最終交鋒。
被幾世代戰事所逼瘋的士兵嚎吼聲開啟了最後一場衝突。數發巫術響雷轟擊了敵軍的中心。
烏金驚恐地看著他不熟悉的次等龍族戰鬥並在第一次衝鋒時殞落。阿卡迪薩巴斯擁有高明的統率技巧,來回飛行以抵擋這裡的側擊行動以及那裡的巫術襲擊。不過尼可總是能夠反擊他,不停地巡視戰鬥陣線,而成群的士兵與術士們則奮力爭取在前線作戰的榮耀以讓他看見。他們兩人都如此專注在戰事上,以致於沒人注意到他,懸浮在他們上方的高空中。
在一陣突如其來的怒意下,加上為自己離開了這麼久而感到羞愧,這條龍展開翅膀向下俯衝。在他的旅程中,他已習得巫術不讓自己受到鐵製長矛與致命魔法網的傷害,於是他便衝向兩軍之間並在一陣無形的閃爍火光裡展開翅膀懸浮在他們之間,宛如一個亡靈。受到驚嚇的部隊往後撤退。甚至連他那不停交戰的手足們也因他的無預警現身而感到震驚不已,進而停止戰鬥。
既然他已經吸引了他們的注意,這條龍便嘶喊著。「尼可!阿卡迪!你們必須終止這一切!這是錯的!」
「我只為了保護我的人民而戰鬥!」阿卡迪以憤怒的咆哮回應。不過他十分精明,立刻就發現尼可已經把注意力從他和他的軍隊轉移到這位闖入者身上。
就在這條龍盤旋在他們之間的當下,阿卡迪號令他剩餘的殘破軍隊全面撤退。
另一群軍隊陣線正等待它的指令。
尼可震驚地凝視著他面前的復靈。
「這是什麼巫術?」他質問道。「烏金已經死了。」
「不是巫術。你不認得我了嗎,尼可?」
「這是阿卡迪操弄的某種詛咒魔法!」
他向前衝刺並且,噴出一道火焰轟擊,試圖抹除這個幻影。但烏金的魔法非常強大,由魔法的所有光譜交織而成。尼可的怒火無害地流過並消散於空氣中。感到害怕的軍隊依然堅守陣地,甚至是那些被燃燒的火花擊中並在倒下時痛苦地扭動著的人。
「尼可!住手!真的是我。」
「你已經死了。我看見你被人類的邪惡巫術轟擊殲滅。那是他們為了報復我的勝利而摧毀我最鍾愛之物。但我已為你復仇。我要讓這個世界配得上你那和平與和諧的願景。」
「你把這一切稱為和平與和諧嗎?」
「它會的。來看看我的成就吧。來吧,烏金。」
他的話語如此真誠。不過他卻拋下了他的士兵,讓他們自行接載他們的亡者與傷者。來自阿卡迪撤退軍隊的斥侯前去回報這份突然轉變的情勢,講述勝利者是如何放棄在戰場上的優勢。但烏金卻無法留下來觀察阿卡迪打算做什麼,更別說是花上一小時或一天的時間與他的哥哥交談,詢問在他離開後的數年或數世紀裡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來這裡尋找尼可的,於是他便跟著他的雙胞兄弟。他們飛越杰姆拉的平原與山脈,然後跨越海洋,穿過其他島嶼和大陸。多明納里亞十分美麗,充滿層層疊疊的瀑布與壯麗的山脊,活化了空氣的蔥翠牧地與繁盛森林,還有色彩繽紛的礁石與閃閃發亮的沙礫島嶼。但在這些驚奇地貌之間卻散布著戰爭的殘跡:凋萎的原野,燒灼的村落,四散的骸骨。甚至連大地也被不顧後果而施放的可怕魔法扭曲:阻塞的河流淹沒了不幸的聚落,峽谷掘穿了平和的平原,雪崩掩埋了寧靜的山谷。尼可帶著滿足的笑容審視這片地貌,看似沒注意到任何駭人的毀滅。
「你是否曾猜想過這世界是個如此遼闊的地方,烏金?我去過每個地方,無論地方大小都有我的足跡。其中有半數現在歸我統治,因為我已從最卑微攀升至最偉大的位置。整個多明納里亞都將臣服於我。現在沒有人敢稱我為「最卑微」的了。而且你將歸返和我共享這份勝利。」
至少他們來到他們誕生的大陸,以及他們出生的山區。火山口峰頂一片荒蕪,除了一雙由大理石製成的彎角,讓這座山看起來好像自己長了角似的。
「這裡不是有一座殿堂嗎?」烏金問道。
「曾經有,在很久以前,不過我發現人形生物並不適合涉足頂峰聖地,只專屬於龍族。專屬於我。」他優雅地著陸,騰出空間讓烏金降落在他身旁。「也專屬於你。我非常想念你,烏金。我的痛苦擊垮了我。我每一天都想到你,想知道你發生什麼事以及你過得怎樣。所以,告訴我,你覺得我的王國如何?」
烏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而終於,沉浸在自我輝煌中的尼可,發現他沒有回應。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吧,兄弟。難道我的成就還不夠卓越嗎?就算是你也得承認沒有任何生物擁有像我這樣大的權力。」
話語宛如火焰般湧出。「你試圖用心靈的伎倆影響我。你怎麼能這樣,尼可?你對其他人使用這麼可怕的魔法已經夠糟了,更何況是我,你的雙胞兄弟!」
「當對你使用這個『伎倆』的時候你才這麼討厭它。」尼可輕聲笑著。「我當時很年輕,正在測試我的力量。但我現在已不需要如此缺乏自信了。我是萬物的皇帝,或者指日可待。」
「萬物?你認為這就是一切?」烏金大笑,他的內心翻騰著某種他不理解的憤怒。
尼可感到憤憤不滿,一邊轉頭怒瞪著他。「你為什麼要笑?權力沒什麼好嘲笑的。」
「這只是無數斷片中的一個。當然,對在這裡出生與死亡的人而言非常重要。不過相較於世界之外的多重宇宙,就像是宣稱這座山是一整世界,但它卻只不過是整個宇宙中一個渺小的部分而已。」
「你在說什麼?」
「我說的是忒祝祈教我的…」
「那個年老人類早就死了,而且她那喋喋不休的智慧也已化為塵土。當時你和我還在這裡。」
「如果那是你的想法,那麼你就不懂死亡或智慧。我對你期望很高呀,尼可。難道你真的相信這些瑣碎的戰事與征討對廣大無邊的宇宙來說有什麼意義嗎?」
尼可從鼻孔吐出火花。一縷含硫的煙自他口中嘶嘶地升起。但他卻沉默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狂風在山頂哭號。白雪開始飄落。落在龍鱗上的雪花立刻就蒸散了。水滴落到岩石上,形成小水坑後便凍結。在遙遠的下方,白雪將四周的地貌覆上一件冬天的披風。烏金不記得這裡曾經有這麼冷,但那溫和的氣候顯然已改變。甚至連曾經雄偉的城市看似也已消融,被包覆著傾頹塔樓與毀壞尊貴大道的森林佔據。在遠方,一圈要塞阻擋了所有通往山麓的道路。越過這些哨站有許多在頂部裝設巨角的殿堂,而越過這些殿堂則有一些城鎮,因過於遙遠而只有龍目能夠看見。但每一座要塞與殿堂和城鎮都朝內面向山脈,彷彿對尼可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張臉都朝向他以讚頌他。
尼可以一種沉思的惆悵語調說道。「難道你回來只是為了要羞辱我嗎?我以為我們是雙胞兄弟,不是對手!」
被這句話哄騙,烏金軟化了。「我們當然是雙胞兄弟,不是對手。我們的連結,我們的手足之情,是我回來找你的唯一理由。如果我沒回來,我就會探索所有位於這個小世界之外的奇觀。」
尼可瞇起眼睛,露出了帶著擔憂的好奇神情。「你去過哪裡?如果不是一道巫術咒語讓你在我眼前的一陣魔法漣漪中消失,那麼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現在是一個鵬洛客了。」
尼可凝視著他,目光閃爍。
「我甚至不確定有其他和我一樣的人。我還沒發現其他任何能夠穿梭世界的生物。」
尼可眨了眨眼卻不發一語。
「我不知道它發生的原因,或是方法。只知道我原本在多明納里亞,面對著你,然後突然間,我被拋出了這個時空。當時我非常震驚。我感到徬徨困惑。不過我後來發現了許多時空,許多世界。它們被一片陰暗的空間聯繫著,一切都結附在這張黑暗的巨網上。藉由進出這張網,我能夠從一個世界通往另一個。我看見了好多奇景呀!我造訪了一百個世界。統治多明納里亞對一個目光短淺的暴君來說倒是無可非議,就像殺了我們受傷的姊妹並相信這會使他變得神聖無敵的那位老族長。但他和他那些卑劣的傳人們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暴君,相較於永恆無垠的…」

「你是在拿我和那些被我輕鬆摧毀的可悲、脆弱、短命的人類做比較嗎?」這些話出現在最微弱的低語聲中。
「當我看著你在這些與我們龍族同胞的無意義交戰中所造成的後果時嗎?聽你誇耀這一切就像個小孩把殺了一隻蒼蠅說成殺了一條強大的龍的時候嗎?沒錯,我確實把你和如此可悲的生物做比較。至少他們懂的不多。你應該很清楚。」
「你會這麼做已經多久了?」
「從那天開始。你試圖操弄我的思緒的那天。」
「以人形生物的時間標準,那一天已經是四或五千年前的事了。你竟然到現在才想要回來?難道你從未對自己說過,我一定要和我的兄弟分享穿梭時空這個重大的發現嗎,我的雙胞兄弟?」
「我要怎麼信任你?你曾試圖操控我…」
「告訴我如何穿越時空。帶我一起走。」
烏金急切地說。「你把意志集中在你內心的火花然後
他突然停了下來。是誕生於他體內的火花給予了他穿梭時空的能力。沒有火花,世界之間的通道就只是一扇緊閉的門。
「你說不出來,對吧?」尼可冷笑著。「這一切都是謊言,不是嗎?你這段時間一直躲在一個懦夫的聖殿裡。現在當我幾乎征服了這個世界時─唯一存在的世界─你就像個飢渴的老鼠般地回來了,打算竊取我的榮耀並將它據為己有。」
「你不相信我。」
「我當然不相信你。你是個騙子。你一直都是個懦夫和騙子。這是個漫天大謊,源自於你那恐懼、貪婪的心,因為我已完成所有你欠缺意志的勇氣或力量來實現的事。總是在針對我,不是嗎,烏金?」
「在一切發生的事物中,你只看見自己。你怎麼了?」
「我沒事。我一直都是這樣。」
「好,或許真是如此。或許我才是那個一直對自己說謊的人,認為你已經變好了。」
「謊言就是你一直自認為比我優秀。你才是操弄者,烏金。不是我。我做的事只是為了幫助我們存活。我一直相信你和我們被殺害的姊妹。除了懦弱地躲起來,拋棄我,你還做了什麼?你只有在我為了讓我們能夠安全地生活在這個世界而完成所有艱難的工作後才爬回來。」
「你說的對。我應該永遠不要回來。所以就這樣吧。好好享用你對多明納里亞的統治權吧。你只會知道這裡,永遠也無法觸及那些未知的世界。」
感到怒火中燒與心碎,烏金消失在一陣無形的火焰漣漪中。
一股震動使奈瓦朝側邊翻倒。隨著她的背撞上冰冷的晶石壁,她也震驚地張開了眼睛。她的手放開了百夏的手指,連結也隨之中斷。她的雙胞姊妹依然在呼吸,胸口緩緩地上下起伏。她的眼睛在緊閉的眼皮底下不安地移動,不停來回轉動彷彿要將無止盡的景象盡收眼底。她被困在回憶中,或是虛假的夢境裡呢?她們所見之物是否為真,又或是一種虛影?
一個獵人相信眼前的證據:蹄或爪子的壓印,斷草揭露的小徑,地面與空氣裡的氣味,一頭野獸經過時的沙沙聲響或牠的聲音標記了牠的位置。怎麼會有人相信從遠古或從未知來源冒出的夢境所傳遞的故事?要是它們全都是謊言呢?
外面傳來腳步聲,緊接著是鵝卵石在道路上滑動的聲音。她低頭探出細小的開口,看見祖母正從彎道上急速趕來。她緊抓著長矛慌忙地跑了出去。
「祖母。」她壓低了聲音,一邊緊張地往天空瞥視,不過她說不出原因,就只是感覺到背上的一股刺痛,沿著她的脖子直豎的汗毛,彷彿這個獵人正被一個比任何人類更巨大、致命的掠食者追捕著。
「奈瓦!」祖母牢牢地抓住她的肩膀,以一種罕見的擔憂神情搖晃著她。「為什麼妳們兩個要離開安全的洞窟?百夏在哪裡?」
奈瓦指向位於低處的入口與昏暗的內部。「我試著阻止她,但妳知道她是怎樣的人。靈龍引誘她來到這下面並把她困在一個具有廣闊水域的怪異領域中,就像一面鏡子。」
「把她困住?」
「我跟著她進去。當我握住她的手時,我也陷入沉眠。我看見她眼中的景象,感覺像是回憶的夢境。接著我翻身中止了我們之間的連結,於是我就醒過來了。可是她還在沉睡。就好像她停不下來。」
「靈龍正試著要跟我們交談。」
「烏金已經死了。」
「妳一直這麼說,但先祖們永遠不會真正地離開我們,除非妳捨棄對他們的回憶。妳看見了什麼?」
奈瓦不是個說書人。跟獵人一樣,她反而有效率地描述了那奇怪的地貌與飄浮的氣泡。祖母仔細地聆聽著並且,在奈瓦說完後,默默地站著,那專注的表情彷彿就像在話語中獵捕她正在尋找的祕密。
終於,奈瓦無法再承受她的沉默並插嘴說道。「可是這一切有什麼意義?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
「看來烏金終究沒死。但也尚未清醒。我的結論是靈龍正試著以他唯一能夠辦到的方式與我們溝通,正如先祖們有時會透過夢境或幻視傳達。風民與魔法之風具有較深的調和,所以他從沉眠裡向他們送出一份幻視。他們呼喚百夏來找他,知道她的低語者身分能夠用心靈對談。」她稍作停頓。「妳和我都辦不到,奈瓦。並不是妳和我缺少了什麼。那只表示百夏有她自己的生命之途。」
「把一份幻視傳遞給妳,要妳來到這座墳墓?」

「或許吧。泰靖的師父一定是個強大的祭師。所以,他也能夠接收到一份幻視,也因此而派泰靖前來告訴我靈龍在很久以前告訴潔斯凱族的故事。那個故事一定非常重要,包括了一部分靈龍想要我知道的事。但我要從這些暗示與重大事件裡得到什麼資訊呢?烏金到底要我看見什麼?」
「要是這一切都是謊言呢,祖母?夢境可以是謊言。古老的故事可以是謊言。」
祖母抓住她的下巴並迫使她看著她,並在仔細檢視她的臉時直視著她的眼睛。「妳的瞳孔看起來正常。妳在腦中有聽見一道低語聲嗎?」
「那是什麼意思?沒有!妳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梅芙菈和其他人幾乎肯定是死了。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化成梅芙菈的形體,但若我的懷疑屬實,那麼我們就有極大的危險了。」
祖母平淡的說話方式使奈瓦打了一股恐懼的冷顫,像是一隻冰冷的蠕蟲啃咬著她的心使她感到暈眩。「什麼危險?其他人在哪裡?」
「躲在聖穴裡。妳必須上去和他們待在一起。」
「妳打算做什麼?」
「我不確定,」祖母說。這四個字是奈瓦這輩子聽過最駭人的事,因為祖母總是知道該怎麼辦。「靈龍試著要給我們的警告或許已經來得太遲了,但我必須親自嘗試與烏金溝通以找出他的目的。如果你說的是真的,或許我可以透過百夏接觸他的夢境。」
一陣噪音使她抬起頭。她們兩人都直盯著峽谷的外緣,再移向高處,接著越過它看著晴空的迷人藍色光澤。太陽來到天頂。沒有東西在移動,連一隻鳥或昆蟲都沒有。
「我可愛的孩子,」祖母以一種低沉的聲音說道,因突如其來的情緒而嘶啞。她親了她兩側的臉頰。「快點走。悄悄地走。妳懂我的意思嗎?別讓任何東西使妳分心。」
她爬入這個狹小的開口,消失在晶石結構物裡面。奈瓦腳下的地面傳來一陣顫抖,宛如來自遠方的一場地震,或是一隻生物在地底深處翻滾而產生的震動。
「祖母?」她悄悄說著。
無人回應。
一股恐懼感使腎上腺素流經她的肌肉直到她開始發抖。咬了一下嘴唇,她深呼吸以驅逐這份恐懼浪潮,但她卻不禁想著她在世上最愛的兩個人正在沉眠且毫不知情,全然地無助。她把那片破碎的水晶安置在入口處以隱藏它,但卻沒有將它固定住好讓它能夠輕易地從裡面移開。在沿著小徑往上走了十步之後,她回頭看。從這個距離,晶石表面看似光滑完整,她突然開始害怕自己已經不小心把她們困在裡面,擔心她們會奮力逃脫但最後卻被困在她一手造成的牢籠裡。要是她們渴死在靈龍的遺骨旁呢?
她就只要回去再檢查一次
她用眼角的餘光瞥見一閃而過的人影。她轉身,用長矛指著小徑。一名女子從一塊隆起的岩石後方現身,通過最後一條彎道,接著這條道路便筆直地探往峽谷基部。她擁有懷孕的巨大身形,但腳步卻特別輕盈,既強壯又優雅,一點也不笨重。奈瓦立刻就認出她了。經常在阿亞戈的年度聚會上看見梅芙菈的臉孔,許多狩獵隊伍與家族必須出席這場安塔卡的盛會。她的祖母與祖母的祖母是親姊妹,而且她本身也是個狩獵首領,既聰明又冷靜,是少數真正受到祖母敬重的人之一。
梅芙菈面露笑容,一邊看著奈瓦。那是一道如此友善、親切的笑容,如此讓人安心。
「妳好,小妹。我遠道而來尋找妳和妳的家人,同時也要尋找一些我自己的家人。」
「妳是誰?」她的聲音裡突然透出恐懼並穿過她的肌膚,儘管她說不出原因。
「難道我們不認識彼此嗎?妳的名字和家族是什麼?」
在奈瓦意識到要說話之前,她的嘴巴就張開了。「我是奈瓦,婭紹娃之女琦亞卡的女兒。」
「婭紹娃!哎呀,那正是我在尋找的婭紹娃。她不在這裡嗎?難道我不是看見她往下走向這個地方嗎?」
「這裡什麼都沒有,正如妳所見。」奈瓦集中精神想移動她的右腳,任何能夠脫身的辦法,但那隻腳卻無法移動。一陣反胃的恐懼感從她的胃部爬上來,她開始深呼吸直到她能夠說出可理解的字。「就只有這些晶石,覆蓋著一條在很久以前死去的巨龍遺骨。」
「不是很久以前。是片刻之間。一口氣之間。」
「在我出生之前,」奈瓦說。
「啊,妳非常年輕,只不過是一隻幼雛。」
「妳是誰?」
「妳不認得我嗎?」
到了這個時候百夏已開始喘氣,彷彿她正在奔跑而且停不下來,但實際上她卻完全沒有移動。那位戴著梅芙菈臉孔的懷孕女子逐漸往下走,逐漸逼近。她受過的獵人訓練響起了所有警鐘:這個女子沒有任何毛毯或汗水的氣味,在她裸露的臉頰上沒有閃耀的油光。風也沒有吹起她的任何一束黑髮。
她沒有傳出腳步聲,甚至連最輕微的摩擦聲都沒有。
她的雙腳沒有碰觸地面,她的靴跟與粗糙的塵土隔著一根手指寬度的距離。
祖母曾說過什麼?虛影可能會讓我們看見原本不存在之物。
「妳是誰?」奈瓦不顧一切地複述,她的手緊握著矛桿,並抬起長矛指向那個女子,而她則持續用那詭異的方式滑下小徑。「妳不是梅芙菈。妳不是我的親族。」
這個孕婦停了下來。她以極為緩慢的速度眨了一下她的眼皮,看似白天都將轉為黃昏。然後她露出笑容,有點過於開懷,有點過於歡樂,有點過於溫暖。
「一隻聰明的幼雛,觀察力如此敏銳。婭紹娃在哪裡?」
「不在這裡,正如妳所見,」奈瓦堅決地說,儘管她在努力挺直身體的同時感到暈眩。「妳是誰?妳不是梅芙菈。妳的腳甚至沒碰到地面。」
「真聰明!」
這位孕婦的笑聲填滿了峽谷,在它的高壁上不停迴盪直到奈瓦跪了下來並且,拋下她的長矛,用雙手捂住耳朵。笑聲突然中止,同時這個女子的笑容愈來愈寬,繞著她的頭往後捲起,裂開的嘴巴宛如被一把刀割開似地露出了喉嚨,嘴唇剝離吞噬了她的頭然後是她的肩膀,接著她以一種駭人的扭曲誕生方式裡外翻轉。但從這個女子的融化身軀裡出現的形體卻不停扭曲延伸,如此貪婪地生長著,彷彿這個新生物想要吞噬整座天空。
有一條龍從這個虛影中延展而出,相較之下,如此壯麗的生物或許使她對安塔卡的記憶顯得微不足道。如此巨大的身軀遮擋了太陽,而陽光則從兩側勾畫他的形體讓他閃閃發光。他四周折射出彩虹,在空中投射出彩色圓弧彷彿正在慶祝他的到來。奈瓦震驚地仰頭注視那雙彎角,因她在晶石內共享的怪異回憶而感到相當熟悉。一顆耀眼的蛋形寶石飄浮於雙角之間,一邊緩慢地、催眠般地轉動著。
「一切都會好轉,」巨龍以他那輕柔、哄騙的聲音說道。「妳現在已經安全了,小奈瓦。妳的所有煩惱都會解決。妳想要的一切都會成真,持續一輩子。相信我。我只需要一樣東西。一樣小小的東西。」
她絕不屈服。她絕不退縮。絕不。「你想要什麼?」
「我要烏金。」
「烏金已經死了。」
「當我第一次殺他時我也是這麼認為,但他終究還是沒死。這次我回來進行確認。妳就是那個無畏的獵人,很快地將會以最強大的屠龍者聞名於世,而且妳即將幫助我永遠地摧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