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軍壓境|第二集:屏息以待
茜卓討厭等待。
她討厭這一切:他們都被關在安全屋裡;每天都有其他的鵬洛客報到,等著聽最壞的消息;知道打擊即將來臨,卻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發生,這種極度痛苦的感覺。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中,他們毫無過真正意義上的生活。
他們一直在等待。
畢竟這就是計畫。他們將在莉蓮娜於多明納尼亞的小木屋等上二週。雖然她發誓這些只是為即將重建的維斯莊園準備的簡單安置點,但它們擠滿了那種會讓惡魔三思而後行的防護措施。茜卓根本不知道莉蓮娜竟然知道這麼多防護措施。在追問下,莉蓮娜只是說她學會了保護自己的投資。
在這兩週結束時,如果他們還沒有得到任何消息,那麼他們就會假設所有人都死了,並採取相應措施。如果他們在那之前得到消息—嗯,他們會根據消息採取行動。如果是好消息,他們就會告訴其他人沒什麼好擔心的。
如果不是好消息,他們會告訴其他人準備應戰。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接受等待—比她更好。薇薇安外出的次數遠比待在室內多,這給了大家一點喘息的空間。她的廚藝也棒極了。芮恩也經常外出,但不會離得太遠。據她說,等待對她來說還行,但茜卓知道她越來越無精打采。芮恩也許是一個樹靈,但她的內心也有一團火,而火總是渴望更多。
還有莉蓮娜,她和茜卓一樣討厭等待。
他們並沒有真正地談論這回事,因為談論它就像撕開傷口一樣,但他們彼此之間都感覺的到。當下午 茜卓和芮恩談話後回來,莉蓮娜經常會為她準備好一個故事。有時則是安靜的陪伴—當茜卓等待時,她會坐在那裡讀一些古老的大部頭,或者複習整修計畫。她現在要如何專注於這樣的事情呢?每個人都在努力讓自己變得正常,但什麼都不正常,而且也沒人願意提起。
她從來不問有沒有消息。如果有人來打聽一些消息,通常是莉蓮娜來回答,省去了茜卓的麻煩。
但感覺一天比一天更糟了。就像有一把刀抵著她的皮膚,每天有人把它拽的更深一層。每一滴血都是她未曾大聲說出口之事,是她不敢去想的想法。
非瑞克西亞的武器。黑色礫油。阿耶尼和多美代,永遠失去了他們,和幾個月前的他們是如此不同。一整個時空都是這樣的人—會對別人做出那種事的人。也許把他們當成人就錯了。
她想要反擊。至少,如果她於激戰關頭身處其中,她會知道發生了什麼,即使答案並不好。最近,沒有一個答案是好的。如果妮莎是
最重要的是,她希望等待快點結束。
現在,她會和芮恩一起消磨時間。
「你必須專注於你的呼吸。火需要空氣,就和我們一樣,」茜卓說。當事情變得糟糕的時候,雅亞經常這樣告訴她,讓她平靜下來:如果她能控制她的呼吸,那麼她就能控制她的火,如果她能控制她的火,一切都會好起來。
雅亞死了,阿耶尼殺了她,茜卓不確定是否一切都會好起來。但她只能希望一切都會好起來。芮恩不擅長呼吸。茜卓並不因此瞧不起她—畢竟她是個樹靈。他們大多數沒有肺。
「與人類的呼吸相比,有點難以掌握,」芮恩說。火焰在她粗糙的皮膚之間輕拍著。儘管她一定有痛感,但她聽起來很開心。
「對,」茜卓說。她撓了撓後腦勺。妮莎說的是樹。她甚至可能有很多樹靈朋友。她總知道該說什麼—但她不在這裡。「把它想像成
「好多了,」芮恩說。火焰確實閃爍著—但它並沒有像茜卓想要的那樣退卻。
她把手放在芮恩的肩膀上,感覺這是導師該做的事情,但對於如何指導毫無頭緒。雅亞留給她的教誨太多了。茜卓不確定自己是否都內化了,她該如何把所有這些都傳授給芮恩呢?別人會做得更好,一個更年長的人,
像阿耶尼這樣的人。
茜卓澆熄了這個念頭。
「讓我們一起做吧,」她說。「我就在這裡陪著你。有些火不值得浪費空氣;關鍵是要辨別哪些是。」
「好吧,」芮恩說。「雖然這對火來說似乎很失禮。」
茜卓閉上了眼睛。她吸了一口氣。在她的腦海深處,能聽到賈亞穩定的聲音告訴她,要專注於空氣通過鼻孔的感覺。她重複著這些話,笨拙而不優雅,當它們來到她面前時。你得對著火說話。找出它想做什麼。
接著當泰瓦到來,所發出的粗暴戰爭號角轟鳴聲,像把斧頭一樣落在他們之間。
二人立即朝安全屋望去,看到兩個人影一瘸一拐地走進門。茜卓的呼吸在喉嚨裡停住。
她和芮恩之間不發一語;也沒有必要。茜卓向安全屋走去,向灰暗的天空發射了一顆信號彈,希望這足以引起薇薇安的注意。
儘管茜卓討厭等待,但她發現自己在門口猶豫不決。
只有三個人回來了。可能是前三個,也可能不是。但會是哪三個呢?她在腦子裡一遍一遍地想各種可能性,她恨自己這麼做。有消息總是好的,不管是什麼消息。可是誰在門外等著呢?
如果她待在這裡,她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茜卓吸了一口氣。她閉著眼睛走進安全屋。
「我們對樹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們有自己的樹。它是腐化的、扭曲的—」
「他們超出了我們的計畫。有萬全的對應方針─」
「把現實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
三個聲音。沒有妮莎。又一個損失。
茜卓嚥了口氣。還有別的事要考慮—這個計畫比他們任何一個人都要重要。魁渡,大致上安好,靠在一個半身像上。在她睜開眼睛時,卡婭和泰瓦正癱倒在沙發上,二人身上滿是血跡、污垢和油脂。在所有人中,莉蓮娜正在照顧傷員—她面前的地板放著小瓶的液體。她倒了些在布上,輕輕擦拭泰瓦的傷口。
是莉蓮娜注意到茜卓走了進來。「這不是個好消息。」
「沒覺得是個好消息,」茜卓說。「從來沒見過比這更邪惡的。」泰瓦說。他臉上浮現出一副不安的表情。「他們用從凱德海姆那偷來的世界樹靈華,製造了一個怪物,它甚至不是活的。」
「他們正在用它來入侵其他時空。」卡婭再也坐不住─她站起來,來回踱步。「調動全體大軍。你我前所未見的武器。除了那些機械噩夢,新非瑞克西亞幾乎沒有人類了。很快,它們將無處不在。」

「但我們還有人可以反擊,不是嗎?我們可以把其他時空上的人都叫來,把他們團結起來,擊潰新非瑞克西亞,打倒艾蕾儂,」茜卓在胡言亂語,她心裡清楚這一點,但她停不下來。空氣,她想,空氣—保繼續持呼吸。這一切都是值得的空氣。「這還沒完。這不能就這樣結束。」
卡婭的眼神裡有同情。「不,我們不能這樣做。」
「也許我們應該等薇薇安來了再說,」魁渡插話。
茜卓一點都不喜歡這樣。「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他們是怎麼控制的?」
「我只是說─」卡婭開了頭,盡量讓語氣保持溫柔。
「拜託,卡婭。」茜卓說。她帶著痛苦的聲音讓她很驚訝,「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卡婭吞吐了半天,「他們抓走妮莎。」
就這樣,茜卓忘記了該如何呼吸。她勉強吐出了一口氣。她知道。某種程度上,她知道,當妮莎沒有和這群人一同歸隊時,她就
她還沒來得及說什麼,身後的門就打開了。
「有消息嗎?」薇薇安說。「等等
「技術性遲到,我猜」莉蓮娜說。她繫好泰瓦胸前的繃帶。「他隨時都會現身。」
卡婭閉上眼睛。「不,他不會。」
至少,莉蓮娜的臉上看不出痛苦,她的聲音尖銳而痛楚—和茜卓胸口的傷痛一樣。「別開玩笑。」
「他英勇戰鬥,但這些野獸
「當你的對手從不疲倦,從不犯錯的時候,勇敢就不重要了」,魁渡說。他似乎無法從地上抬起頭來。「或者當你離去到那麼遠的時候。」
「這說不通,」莉蓮娜說。她站起來,拿起一盤小瓶來掩飾顫抖的雙手。「這一切廢話都是他的主意。他不會就這樣失敗。他不會這樣做的。」
「到了最後,我不覺得那是他了。他成了他們其中一員,」魁渡說。
莉蓮娜深呼吸,不想讓任何人注意到。「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沒有時間去糾結於細節,」薇薇安插話。「不管發生了什麼,娜希麗去了贊迪卡,漂萍一定已經逃走了,艾紫培一定已經提前去了塞洛斯─」
「我們看到非瑞克西亞人也帶走了娜希麗,」泰瓦說。
「艾紫培沒能挺過來,」魁渡補充道。「漂萍可能是要回家了,但艾紫培不可能逃出來了。」
「艾紫培提瑞不可能死在新非瑞克西亞」,薇薇安說。
卡婭眉頭深鎖。她的目光掠過莉蓮娜。「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說吧:最後一次見到艾紫培的時候,她的劍正從傑斯的背上穿出來。」她捏了捏鼻樑,然後繼續說道。「那棵亂七八糟的樹已經至少連接了十幾個時空。如果他引爆了同兆,我們可能會失去它們全部。那東西已經滴答滴答地走向末日,那時已經沒有時間了,所以她…」
卡婭的聲音減弱下去,泰瓦再度接了話,「艾紫培跑過他,拿起同兆,穿梭時空衝進黑暗虛空,這是一場高貴的獻祭—她現在肯定在和女武神們開慶功宴。」
「喔,閉嘴,」莉蓮娜噓聲說。
安全屋的氣氛冷下來,傑斯和妮莎都不見了。娜希麗也是。就連艾紫培最後也沒能成功。他們派出的所有人中,只有四個人回來了,而這四人中只有三人在這裡。他們所擔心的一切都成真:非瑞克西亞的入侵正在進行中。
薇薇安的自信姿態不見了,與他們一起坐在地板上面對現實。「這比我想像的還要糟糕。」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唯一原因。你需要明白我們面對的是什麼。」卡婭說。「整個多重宇宙都必須理解。現在就像我說的─」
「好吧,沒有我你們也能繼續前進。」一段帶著奇怪力量的插話突然冒出,意在減弱發話者的動搖。 莉蓮娜已經向門口走過去,「我要給斯翠海文傳個話。」
「你應該聽聽這個故事─」泰瓦開口說,但莉蓮娜已經搖頭了。
「我已經充分瞭解你講述的方式,而我從不接受所謂崇高的犧牲。」
茜卓張開手,然後握緊成拳頭。「如果我們有辦法可以幫助其他人呢?」
茜卓聽人說過莉蓮娜的鋒芒畢露,野心勃勃。這是真的。但同時從某些角度,那些也是。莉蓮娜的頭傾斜角度一點也不鋒利;她眼中的野心,已變成深切的同情。「你想自己回去那兒,對嗎?」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茜卓身上。她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看她的方式—他們一定在想些什麼。她當然知道,她的衝動。茜卓能聽到說教開始的聲音,她對此已經厭倦了。她厭倦了坐在那裡等著世界末日來臨。
「是的。是的,我願意,」她說。「一定有別的辦法可以把世界樹拆掉。你們都表現得好像這一切都玩完了一樣。」
卡婭用手掌後跟壓著眼睛,她吸了一口氣。「我不能讓你回去。」
「讓我?」茜卓說。她朝她走了一步。「你不讓我做任何事。」
「計畫是讓其他人知道發生了什麼,」薇薇安說。她更冷靜,更泰然自若,但她對茜卓的想法沒有任何誤解。「我們可以集結力量,想辦法反擊。但如果我們貿然行動,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你們有很多人可以去做這件事,」茜卓爭辯道。「我們在內有夠多的人。但如果我們繼續對抗已經存在的東西,我們不會有任何進展。我們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否則它們會繼續來襲。」
其他人交換了眼神。至少他們還在想。莉蓮娜,儘管她之前提出抗議,但她還沒有離開——她仍然在茜卓和門之間。她能理解,不是嗎?她一定比這裡的任何人都更明白這是什麼感覺。下一個說話的是卡婭。「茜卓,我明白你的意思。真的,我明白。但你根本無法理解在新非瑞克西亞發生了什麼。這不是你憑空吹噓就能解決的事情。我們為此做了計畫,結果勉強熬過來了。我當了很多年刺客,差點在裡面丟了腦袋。娜希莉對付的是奧札奇,我們也失去了她。如果你去了那裡,你不僅會死——你會被剝去肉體,你的骨頭會被塑造成金屬,你的思想會被扭曲成他們病態的世界觀。下次我們見到你時,你會告訴我們與非瑞克西亞合二為一的樂趣。薇薇安說得對,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儘量避免失去任何人。一旦我們在這裡結束了,你必須回到卡拉德許告訴人們如何準備。這是我們能為他們所做的最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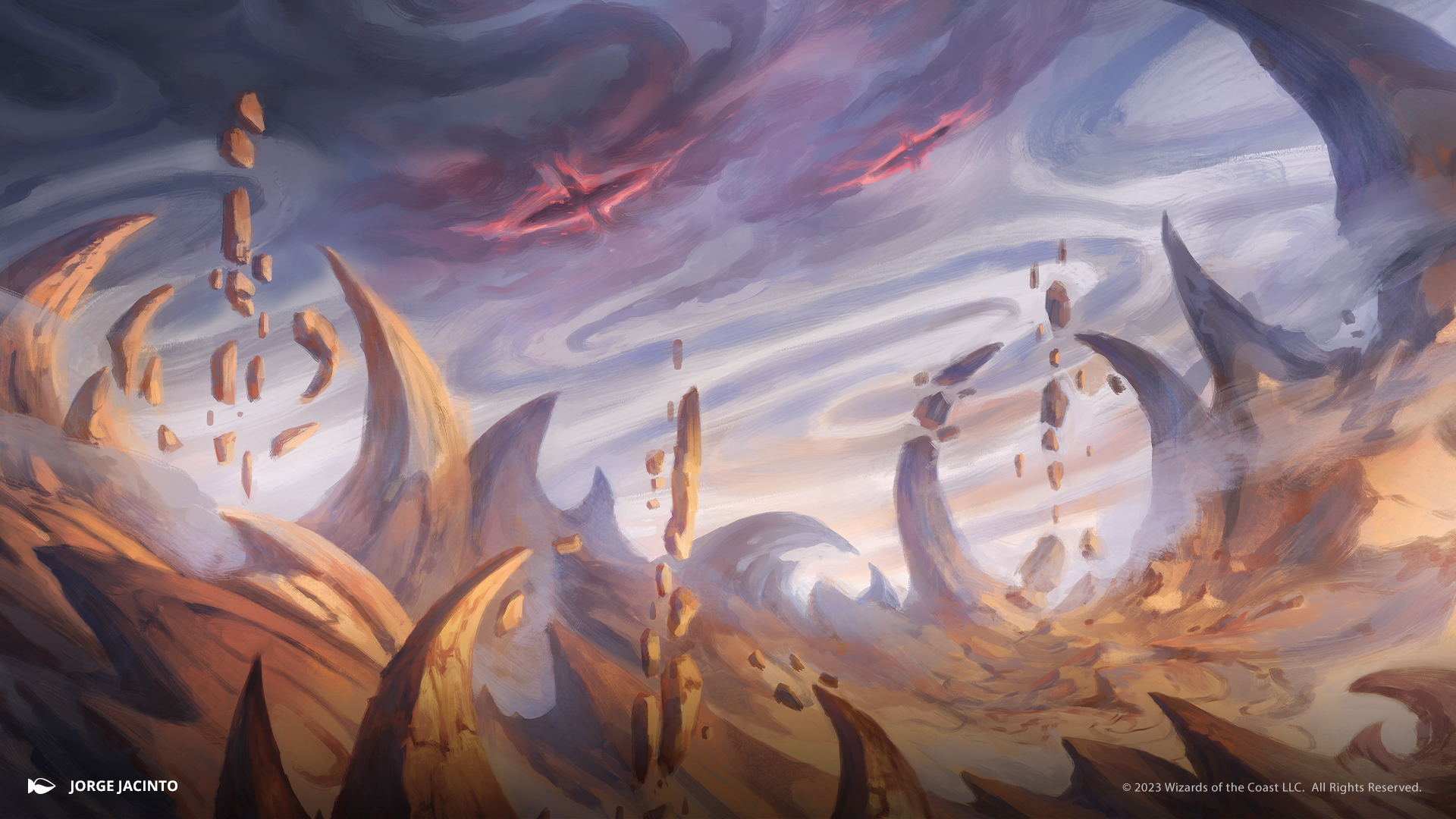
茜卓的大腦還沒來得及阻止,答案就從她嘴裡冒出來了。「你把我當個孩子看。」
「我沒有把你當孩子看。我是想為你著想。這和拉尼卡不一樣。與艾蕾儂的無肉軍團相比,永生者根本不值一提。我知道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你想幫助每個人。你想拯救多重宇宙—沒問題。但有更好的方法來做這件事,而不是貿然毫無章法的跑去,做一個我們全團隊都無法達成的工作。」
卡婭在說些什麼,但茜卓聽到的只是更多的千篇一律。卡婭看不出這有什麼意義。泰瓦必須理解,對吧?他喜歡大的挑戰。但當她與他的眼神交會時,他把目光移開了。
「勇氣值得讚揚,」泰瓦附和道,「但知道哪些戰鬥是你該打的也是如此。卡婭和我只是來告訴你發生了什麼。去需要你的地方,照顧好你自己,死在你的骨骸所在之處。」
「這是每個人的戰鬥,」茜卓說。
「這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發言權,」薇薇安說。「我的意見是,我們不要在我們所知沒用的事上再浪費更多資源。」
「我知道你的感受。承認自己輸了並不容易,」魁渡說。「但我們只是輸掉了這場戰鬥。如果我們能保證家園的安全,我們就贏得了這場戰爭。」
茜卓吸了一口氣。她感覺自己要爆炸了。這是世界上最明顯的事情,他們要麼不能看到,要麼不願看到。「那些被困在新非瑞克西亞的人怎麼辦?難道我們就把他們留在那裡嗎?」
沒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不直接回答。安全屋的沉默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等待,茜卓討厭它,就像她討厭整個情況一樣。如果她現在能把一切都燒掉—如果她能在火焰中找到一個新的開始—那麼她就會這樣做。站在這裡讓她的靈魂發癢。
「告訴我。我們要拋棄他們嗎?」呼吸變得更困難了,或者更容易了—現在的呼吸又大又急,助長了她肚子裡的火,灼熱流淌在她的眼角。
「茜卓,」莉蓮娜說,像雪上的影子一樣溫柔,「她會希望你保持安全,不是嗎?」
她為什麼要這麼說?茜卓一直很努力地不去想這件事,努力讓自己的想像力不受影響,但莉蓮娜釋放了它。想像妮莎在這裡就像召喚火一樣容易,茜卓可以看得很清楚:寫在妮莎的臉上的決心、變成蒼翠天空色的雙眼,她耳朵的角度。她能感覺到妮莎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她能聞到苔蘚和松樹的味道,她能聽到那些話,即使她不想去想像它們。
很痛
天哪,這很痛。
她覺得自己正在他們每一個人面前流血,卻沒有一個人給她任何幫助。
茜卓又吸了一口氣。空氣,她想。只要繼續保持呼吸就可以了。
「當我們失去某人的時候,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記憶,」莉蓮娜說。
「我沒有失去她,」茜卓反擊。
卡婭的惱怒一秒比一秒加深。她累壞了,這體現在她臉上的每一行線條上,「她已經離開了,茜卓。」
「不,她不是。如果我們阻止非瑞克西亞人,那麼我們就能知道如何阻止
「這不僅僅關乎任何一個人,」薇薇安插話道。「我們在照料一片森林,而不只是單一棵樹—」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她說。視野邊緣微弱的光芒告訴她,她正在動怒。她不是故意的,但這很好—甚至可能是好事。所有這些感覺總得有個出口。「你以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命在劫難逃嗎?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回去!如果我們只會逃避他們,我們永遠都贏不了!」
「茜卓─」卡亞開始說,但為時已晚。她已經聽不進去了。
「我要走了,」她說。「如果你想,你可以去警告其他時空,但我不會丟下我們的朋友。」
「你要獨自去?」泰瓦問道。
「既然你們都不去,對,我一個人去,」她說著,回到門口。「但我到了那裡就不會是一個人了。」
「那你的計畫到底是什麼?」魁渡叫道。
茜卓沒有轉身,「把樹拆了,在路上邊走邊釐清所有事來龍去脈,簡單易懂。」
沼地在等待著—莉蓮娜是這群人中最後一個阻擋她的。儘管如此,莉蓮娜並沒有完全擋住她,只是靠在門檻上,注視著。
「你是認真的」,她說。
「是。而且你是認真的想要逃跑,對吧?」
不少人會為了為有機會讓莉蓮娜維斯退縮而殺人,奇怪的是,在茜卓看來,這並不是一場勝利。一點都不像—這是最糟糕的部分。
「你覺得我在做這種事嗎?我不是逃跑,我只是能聽出葬禮鐘聲響起了。祝你的小冒險一切順利。」
「等等,」茜卓說。
但是莉蓮娜沒有停下。她獨自走到沼地上,幾乎沒有回頭看一眼。「哦,沒時間等待了。你自己也是這麼說的。」
今天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茜卓再次張開又合上她的手。她想要爭辯,或者說清楚她真正的意思—如果莉蓮娜來會是一個巨大的幫助,也許他們可以一起找到一些答案,也許直接面對恐懼而不是逃避是件好事。
但是,這將是要求莉蓮娜,成為一個不是她自己的人—而他們兩個人一直都明白,不能這樣要求對方。
莉蓮娜在墨色的水氣中,一眨眼就間就消失了。
茜卓納拉開始向前走。
當眼淚離開她的眼睛時是熱的,但沼地的冷空氣很可能將它們凍結在她的皮膚上,為了不瑟瑟發抖,她調高了暖氣。她不知道在時空穿梭前自己想走多遠。事實上,她根本不需要走遠。只要她想,她就可以這麼做。
但是她想走一會兒。感受一下風,聞聞可怕的沼地味,抬頭看看暗灰色的天空。當她離開時,她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天空。那不是卡拉德許那充滿活力的蔚藍。這裡的雲沒有螺旋形。事實上,這裡根本沒有雲,只有四面八方的灰色泥沼。她聞不到臭氧和攤位食物香味;聽不到市集的喧囂。這地方不是家。這個地方不是她會記得的。
沒關係。她會回來的。還會有其他地方。她會確保這一點,因為當世界樹倒下的時候,他們會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會沒事的,之後。
她在她看到的第一棵樹前停了下來。這並不是一棵很強壯的樹,甚至不是很健康:樹皮已經變黑,樹枝空無一物,粗糙得像利爪掠過天空。但它畢竟是一棵樹,她覺得這可能已經夠好了,可以喘口氣了。茜卓坐在並不存在的樹蔭下,把頭往後仰。
去新非瑞克西亞是正確的選擇。
但是她很害怕。
會沒事的。她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來適應。
也許還需要一秒鐘的哭泣,然後她就會時空穿梭徑直進入一個由曾經的摯友們捍衛的邪惡帝國嘴中。她曾倚賴這些人去推翻那個帝國。他們沒辦法做到。而現在她要一個人去做。
突如其來的涼意和樹葉的晃動告訴她,她並不是一個人。茜卓抽蓄鼻子,皺著眉頭說,「走開。」
「哦,我寧可不要。那我就得回其他人那裡去了。」
啊,是芮恩。至少不是卡婭來勸她不要這麼做。儘管如此,茜卓還是想不出什麼好說的。她試著不去哭泣,因為她有了同伴—但她還是在哭。
「我想幫忙。」
茜卓擦了擦她的鼻尖。「你想嗎?」
「我想。看你和別人說話感覺好奇怪。我以為你說得很有道理。如果一根樹枝腐爛了,你必須先把它砍掉,然後才能評估這棵樹的狀況。」
她從不知道有人能理解她是一種怎樣的解脫。先前,她覺得怒氣都要從體內冒出來了—但現在不同了。就像它融化在地下一樣。儘管如此,她還是得確定芮恩是認真的。「我們不會有任何後援。」
「不要說的那麼肯定,」芮恩說。「我們有七樹妖,我想我們也會有泰菲力。」
泰菲力?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
「你對此感到困惑,對不對?我想那是你臉上的困惑。有時候光看人們的臉,很難分辨他們在想什麼。」
「你猜對了,」茜卓說。「你應該對自己多點信心。如果我們有泰菲力在身邊
「我想我知道,」芮恩說。點了點頭,七樹妖則擺出一考的姿勢。「他又讓自己陷入了困境—但沒有什麼是我們解決不了的。當我們在這裡時,我一直在研究他走過的曲折道路。我知道怎麼接近他,但我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好吧,你不會是自己一個人的,」茜卓說。恐懼也在遠去,因為希望開始抬頭。如果她能把泰菲力從任何地方救出來,他們的勝算就會大大提高。「你會有我,七樹妖,還有我們在那邊找到的其他人。」
但芮恩看向別處,她的手放在七樹妖的樹皮上。「七樹妖為我做了那麼多,但他不能這麼做。他不能把他沒有的力量借給我。一定是火,一定是世界之樹。」
雅亞總是說,與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知道它在與你打交道。你可以引導它,你可以提出建議,你可以給它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最終它總是會做它想做的事,而它想要的東西每一秒都在變化。如果你想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保護你朋友的安全,你就必須和它對話。這與與樹打交道完全相反。
茜卓以前也和妮莎聊過這個。
妮莎曾經告訴她,有時候動盪的成長,那種一下子發生的事情,可能就像火一樣。一開始,茜卓並不相信她。火會破壞,自然會孕育。但後來她看到了在贊迪卡上的狂攪是什麼樣子的,就開始明白了—有時,它是一樣的。她喜歡大自然給她驚喜的感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喜歡聽妮莎談論它。
她曾試圖用妮莎幫助她的方式來幫助芮恩理清頭緒,但教比聽難多了,而芮恩的火焰也不是普通的火焰。她能站在那裡,完全證明了她的力量。如果她真的要釋放它,那麼世界樹可能是唯一能承受它的東西。「你確定嗎?」
「我確定,」她說。「其他人都錯了—那棵樹是活的。我在這裡都能聽到他的歌聲。那是

茜卓露出一個悲傷的小微笑。「英雄,嗯?我也很害怕,但不那麼害怕了,因為我有了同伴。」
「你應該給自己找一個像七樹妖這樣的朋友,」芮恩說。「那樣你就永遠不會感到孤單了。」
除非這位朋友碰巧在一架滿是惡毒敵人的時空迷失了,然後她真的會非常孤單。
茜卓的微笑只顯得更加悲傷—她拉長了微笑,好像要隱藏它。她在小七的樹皮上拍了一下。「我們啟程吧。」
芮恩歪著頭,似乎意識到自己可能說錯話了,但這一瞬間沒有評論的過去了。很快他們就離開了這棵貧瘠的樹的陰影。沒有人來送行。
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他們能看到的人。
但是,有人在監視空地。有人監視著安全屋,監視著屋內擠在一塊尋找目標和方向的人,光線的把戲可能會暴露他們,也可能不會。靈敏的鼻子可能會注意到他們的氣味,也可能不會。但他們就在那裡,觀察著。
所有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很熟悉,就像一首歌詞早已消逝的歌曲。一遍又一遍,他們試著去回憶,然而歌詞卻一閃而過。只有旋律還在:對即將到來的事情的悲歎,一首悲傷的讚歌。
觀察者並不孤單。那裏還有其他同伴,看到,或看不到。觀察者問其中一個:「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答案就像戰爭號角的喇叭聲傳來:我們在這見證末日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