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視烈陽的另一側
華特莉

華特莉當時八歲。
微塵在午後陽光中飄落並以一種橘色的光芒點亮了位於托卡特理陰影下的練習場。十幾位其他的孩童坐在她身旁的石磚上,他們小小的手都緊握著木製的訓練武器。她年輕到認為不得不提出數千個問題,但也年長到知道該等待最佳的時機。於是她便用小小的手緊抓著腳趾坐在地上,等著烈陽帝國的僧侶說完長篇大論。他正在向這群年輕的準戰士們講解烈陽三相,但卻用一種華特莉聽過最為無趣的語調說著。她早已能夠背出這些故事。她喜愛故事。
「在烈陽的另一側有什麼?」她脫口而出。
僧侶眨了眨眼。
華特莉用手擠壓她的腳並保持著堅定的視線。
僧侶嘆了一口氣。「華特莉,有一天妳將會用手中的劍戰鬥並用烈陽之力演說。在另一側有什麼並不重要。」
華特莉厭惡他們提到她的未來。她因為擅於說故事才會參加僧侶與祭師的特別課程,但無法將那段時間用來和其他準戰士們相處卻讓她感到氣惱。
「可是我想知道另一側有什麼,」她說,一邊努力用真正的好奇心來掩飾她的抱怨。
其他準戰士們惱怒地看著。華特莉漲紅了臉。
「華特莉可能會是我們未來的戰士詩人,」她的表弟因提說道,他的聲音比起一位八歲男孩應有的聲音大膽許多。「難道沒有任何關於烈陽另一側的故事是她應該知道的嗎?」
其他孩童都贊同地點了點頭。
僧侶看起來有點慌亂。他把視線移向他們的武術教練以尋求協助,但她就只是聳了聳肩。他皺起眉頭並直視著華特莉的眼睛。
「沒有任何關於烈陽另一側的故事。」
其他的年輕戰士們同時失望地噢了一聲。
僧侶嘆了一口氣。「指稱妳能看見之物。榮耀妳已成就之事,不要浪費時間在未知的事物上。」
華特莉感到困惑。「要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呢?」
僧侶以被孩童環繞的疲倦大人所獨有的挫敗眼神看著武術教練。
武術教練以老練的威嚴拍了拍手並對其他的年輕戰士們說道。「練習生!兩兩一組練習你們的陣形。第一個被擊倒的人要負責清掃工作。」
其餘的孩子們慌亂起身並跑向練習場的另一頭,因被迫在整場演講中噤聲而變得更加興奮地聒噪著。華特莉一動也不動地留在原地,專注地直盯著僧侶。
他嘆了一口氣,接著用稍微帶點父母怒意的眼神看著她。「我們感覺到妳擁有詞語的天賦,華特莉。如果妳選擇成為烈陽帝國的戰士詩人,那麼當妳成功的時候,妳的話語就會成為事實。」
這個女孩皺起眉頭,感到困惑不已。「那是否就表示我在編造故事?」
「不。那表示當妳說故事的時候,妳正在講述某個人的事實。妳的職責就是知道他們的經歷,並且分享它們好讓我們的族人永遠不會忘記妳描述對象的作為。」僧侶的態度十分堅決。「如果妳為了帝國的福祉而走上戰士這條路,妳將會更清楚地看見。妳必須成為自山頂上吶喊的唯一一道聲音。帝國之聲,真正重要事物之聲。」
華特莉咬了一下嘴唇。她不確定成為山頂上的聲音是她真正想要的。她想著僧侶和武術教練,想著她的嬸嬸與叔叔和因提。她想著帝國裡的所有人,並想著有一天他們將會聆聽她講述的真實。
帝國才是真正重要的,她如此確信。而非任何存在於烈陽之外的事物。

安戈斯與華特莉站在一塊空地上,當下方的大地開始劇烈晃動時,他們便蹲伏身體以保持平衡。他們看著歐拉茲卡的黃金尖塔逐漸升高,超越了底下峽谷的林冠。這些尖塔看似將城市往上拉,一路折斷樹林並把大量的泥土與岩石推向一旁。
華特莉驚訝地喘不過氣來。
這座城市比她所能想像得更加美麗 . . .而且它看起來完全不像她在預視裡見到的那座城市。
大地停止晃動,她強忍著淚水。它就在那裡。如房屋般巨大的高聳拱門與雕刻,一座迷宮般的結構用上的黃金比她所見過的數量更多。這個地方看似正隨著魔法搏動。它與她所在之處仍與隔著一段不小的距離,差不多要徒步走上半天,但比起其他任何烈陽帝國的成員,她已是幾世紀以來最接近歐拉茲卡的一位了。
她左側的牛頭怪興奮地吐著鼻息。「早該出現了。」他開始踩著沉重的步伐下山,意志堅決並且感到不耐煩。
華特莉想起了她的任務,於是便趕上前去。
她的心跳加速。她已經找到它了,但那是否表示她需要折返呢?難道她不該親自探索內部以尋找永生聖陽嗎?華特莉試著要忍住她的欣喜但卻失敗了-一抹傻笑出現在她的臉上。
「所以妳像個女僮僕般地聽命尋找黃金城?」安戈斯譏笑著。
華特莉迅速回到現實。她收起她的笑容。「我的皇帝交付我這項任務。那是我們先祖的家園,我們才是依夏蘭正統的統治者。」
樹林逐漸向他們靠攏。隨著他們走進叢林林冠的陰影中,弧形的枝幹開始在頭頂上延伸,而蟲鳴鳥叫則充斥於華特莉的耳中。
安戈斯盯著華特莉。「妳又從此得到什麼?」
「我會得到我應得的頭銜,」華特莉說。「從小我就一直接受成為戰士詩人的訓練。」
安戈斯嗤之以鼻。
華特莉皺眉。「怎樣?」
「一個頭銜無法讓妳自由。」
他揮出一條鎖鏈扯開一根擋路的樹枝。華特莉感到惱火。「你不會懂的。我的職責就是講述我的族人的勝利。」
安戈斯轉頭看著她。「妳還得靠一個頭銜才能辦到嗎?妳的想法就跟一隻螞蟻一樣。」
華特莉覺得被嚴重地冒犯了,但卻不發一語。她知道這個男人的脾氣有多不穩定,而且她不敢激怒這個怪異的新伙伴以免他發動另一波攻擊。
「你說『妳的想法跟螞蟻一樣』是什麼意思?」她問道,刻意保持冷靜。
安戈斯轉動他的肩膀,一邊往左右傾斜著牛頭,發出了關節碰撞聲。「妳只不過是想爬到蟻丘的頂端然後恭賀自己能夠看見這份景致罷了。」
「你把烈陽帝國稱為蟻丘?」
牛頭怪放聲大笑。那是一道低沉的喉音,使華特莉想到一隻不停嘶叫的長頸龍。「烈陽帝國就是一群在蟻丘上的螞蟻,而且川流使和圖瑞琮以及這個時空上的其他每一群白痴都是。」
「那麼,至少你正在同時羞辱我們所有人。」
安戈斯往前伸手將一束巨花梗拉向一側以讓華特莉從底下穿過。「我的族人重視自由更勝過一切。我們為它深深著迷,鵬洛客,而且每個人都知道原因。」他嚴肅地看了她一眼。「妳替自己編了一條套索,裡面除了依稀被人們記得的故事以外什麼也沒有。」
「故事?」她咆哮著。「你說的是我的歷史。你說的是我的生活目標。我的人生致力於尋找正確的語詞,表達我們的集體情感,並用真實與驕傲來保存烈陽帝國的歷史。」
牛頭怪正咯咯地笑著。華特莉強忍著不說話。他儘可能地以一個牛頭怪的方式向她微笑。「那麼川流使呢?難道他們的歷史不值得被記得嗎?」
「這個嘛 . . .是的。我想它值得。不過戰士詩人並不會研讀他們的歷史 . . .」
「妳們互相殘殺只為了爭奪誰足夠強大來決定什麼是歷史。爭吵不休只為了決定將由誰統治,但卻沒有人擁有真正的自由。妳們憑什麼說自己是對的,笨蛋?」
華特莉感到相當矛盾。
她納悶安戈斯自以為是誰竟然如此不客氣地跟她說話。他既粗魯又無禮,但如果他說的是實話,他便知道華特莉從未想像過的事。如果他來自一個不同的世界,或許那裡的一切都截然不同。華特莉覺得自己像個小孩,堅持己見又魯莽,並大膽地宣稱自己的重要性。她討厭有人暗示她應該要更明白事理,因為老實說,她怎麼會知道呢?她的人生之途兩旁都排列著她的視線無法翻閱的高牆。
一陣顫抖貫穿了她的肩膀。
安戈斯在前方停了下來。他轉頭看著華特莉。
「妳也感覺到了嗎?」
她點了點頭。一股細微的刺痛感沿著她的頸部竄下,儘管叢林十分溫暖,她仍打了個冷顫。
安戈斯抽動耳朵。「跟我來,」他說。
天啊,他有夠無禮,華特莉惱火地想著。
牛頭怪靜止不動,接著華特莉感覺到她前方突然爆發一股熱氣。這個牛頭怪正在施放一道咒語。不對,是某種不一樣的東西。隨著如暖煤般的光芒自內部點亮了安戈斯的身體,她才明白他要她以之前只嘗試過一次的方式跟隨他。
華特莉集中精神。她試著回想起如何窺視烈陽的另一側。
突然間她想起來了,這個感覺沿著她的皮膚往下送出一道顫抖並且拉扯著她的胸口。它既可怕又熟悉,就像是試圖完成後手翻,或是無法接觸池底的游泳,接著華特莉便看著她的肌膚開始閃耀著午後的耀眼陽光。她的感知搖晃,然後她向前傾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領域。它現在已變得熟悉,一座充滿顏色與光芒的耀眼風暴,而安戈斯則在她前方。他正在向前走,探往了一個出口。
華特莉的雙腳離開叢林地面並踏上了虛空。有東西支撐她的身體,但這裡的物質卻缺少重量或目的。她看見兩側藍色的氣流,而且每一個腳步都顫動著她未曾感應過的能量。時間在這裡並不重要。
安戈斯示意她窺看他面前的一個出口。這個牛頭怪依然具有一種燃燒了數小時的壁爐魔法效應,而華特莉則意識到她一定是因為太過明亮而使他無法直視。
她的視線穿過了那扇在空氣中劃出的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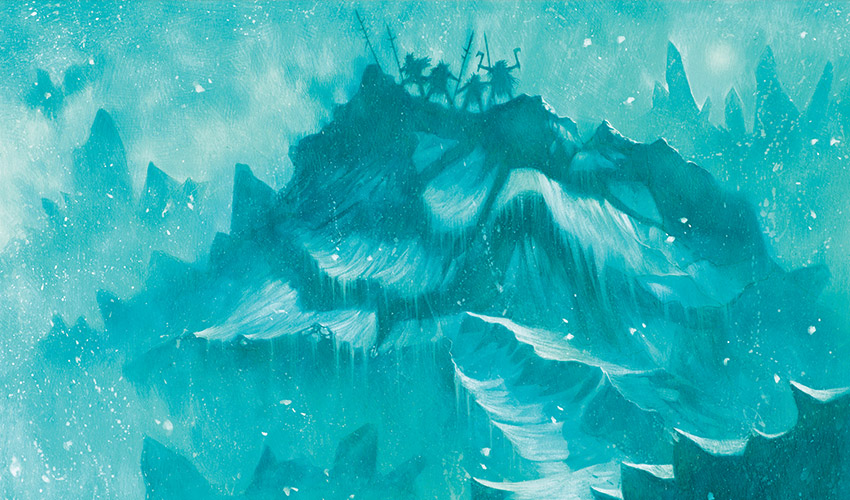
那裡有一種她從未感受過的寒冷。群山探向翻騰的雲朵,陰沉的天空則靜靜地落下了點點雪白。
華特莉感到深深著迷。她把身體往前傾,但立刻就被-劇烈地-拉了回來。
華特莉扯裂空間與顏色並穿越存在的結構,往後墜回到叢林的黏膩濕冷與潮溼的泥土惡臭,最後四腳朝天地倒在地上。
現已更為熟悉的三角形與其內部圓環則閃耀於她的頭頂上。
安戈斯正站在她附近。更習慣於這類魔法驅逐,他早已對這份衝擊做好準備。他低頭看著她,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耀眼三角形正懸浮在他的頭頂上方,同時他的牛類眼睛則擺出一副我早就說過了的神情。
「我們一定很接近那個把我們鎖在這個時空上的東西了,」他咕噥著說。
華特莉顫抖著吐出一口氣。「那裡是什麼地方?」
「凱德海姆,」安戈斯強而有力地說著。「另一座時空。現在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華特莉搖了搖頭。
安戈斯哼了一下鼻息。「自由就從知道妳被困住的時候開始。」
午後轉為傍晚,華特莉與安戈斯並肩而行。他們快步走著,因為華特莉知道如何輕鬆地穿過這片雨林。他們愈靠近黃金城,周圍景觀的變化就愈大。樹葉閃爍著黃金的光芒,而大地的裂隙則造成了通往深處黃金通道的深邃裂口。
華特莉為她打冷顫的強度感到擔憂。安戈斯喃喃說著永生聖陽可能與鵬洛客的魔法有關,而華特莉則嘆了一口氣。有太多人認為永生聖陽能做太多不同的事了。不可能他們所有人都是對的。華特莉一度詢問安戈斯當他能夠離開這個時空的時候,他第一個想去的地方是哪裡。「我想要看看我的女兒們」便是他簡潔的回覆。
華特莉被他的脆弱感動。「距離你上次見到她們已經過了多久?」
「十四年,」安戈斯咆哮著。片刻之間,華特莉被打動了。她正打算表達她的惋惜,但卻被安戈斯的補充說明打斷了:「她們會欣喜地啜飲妳們皇帝的血,笨蛋。」
如果有任何東西能夠把華特莉拋出這個世界,光是安戈斯的人格就能辦到。
他們來到一座自地面上冒出的建築物前,一座中等大小的神殿。正面裝飾著一片寬廣圖案-是一隻蝙蝠,自岩石的皺摺中雕出了牠那駭人的臉孔。這棟建築的傾頹程度使華特莉推測這並非歐拉茲卡的一部分,而是建造於其附近的一座墳墓。這座墳墓感覺上相當不合時宜,它怪異地取代了叢林的內部。非常引人注目,令人不安。
華特莉放慢腳步直到停下。
她記起了一則古老的故事,一則早已被大部分人遺忘的故事,但她卻還記得。烈陽帝國的戰士詩人絕對不會忘記。
「東方的蝙蝠,」她低語著。
安戈斯抽動了一下耳朵。「什麼蝙蝠?」
華特莉指向他們面前的建築。它爬滿了藤蔓並且飽經風霜,而前門則被雜亂地打開一條縫。「有一則傳說提到東方的蝙蝠遇見了阿洛佐茲 . . .」
牛頭怪咕噥了一聲。「傳說中的蝙蝠是怎麼停下來的?」
「她施咒讓自己陷入長眠。」
華特莉朝入口走去,因想到能夠探查這座神殿而出神。如果歐拉茲卡已甦醒,或許這個地方也 . . .
「妳在做什麼?!」安戈斯大喊著。
我正在窺視烈陽的另一側有什麼,華特莉帶著笑容在心裡想著。
她靠近神殿的開口,但卻突然震驚地往後退,同時有一隻蒼白的手正從神殿內部伸出。華特莉目瞪口呆地看著另一隻女性的手溫和地抓住了黃金門板的側邊。
華特莉馬上默默施放一道咒語召喚離他們最近的恐龍。她的心跳隨著她送出召喚而猛烈跳動,接著她便看著這隻手抬起門板並將它從神殿的入口處移開。
在這個人影走入陽光下的同時,華特莉的驚慌隨之消散,並且她驚訝地合不攏嘴。

無庸置疑,她是個吸血鬼,擁有一頭長捲髮以及一張掩飾了她族人那致命本性的年輕臉孔。她具有一般身高,或許比華特莉自己稍矮一點,但在舉手投足間卻帶有皇室的儀態。
華特莉喘不過氣來。她瞥了安戈斯一眼,期待他向前衝鋒殺敵,但他卻跟她一樣一動也不動地站著。
「妳是聖依蓮達,」安戈斯恍惚地說著。「妳就是吸血鬼們成天談論的那個人。」
華特莉因安戈斯知道一則她不知道的傳說而暫時感到焦躁不安。
這個女子從容、緩慢地移動,唇上帶著淺笑將視線自安戈斯移往華特莉。
「歐拉茲卡終於甦醒。」
她的聲音既輕盈又溫和,像是一道劃破寧靜的鈴聲。
華特莉收起她的敬畏之情並握住她的刀。從幾碼的距離外傳來一聲低沉的咆哮,接著華特莉便催促她新召喚的恐龍蜷伏準備出擊。她知道傳說的作用;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故事是如何開始與演化的。幾乎所有的故事都衍生自真實,華特莉很快就了解到東方蝙蝠的傳說是始於幾世紀前的這位真正的吸血鬼。
這個吸血鬼依然保持輕鬆的態度。她直視著華特莉,她的表情正是安詳的化身。
「為何妳要拿起武器?」她以明顯的好奇心問道。
華特莉面露怒容。「我拒絕讓暮影軍團奪走這座城市。你們這些入侵者應該遭受比死亡更慘的命運!」
這位吸血鬼皺起眉頭。她開口想說話,她的舉止受了傷。她那壓低的聲音宛如來自異界。「我們現在成了入侵者?」
「我知道我們族人所有關於妳和你們暮影軍團的故事,」華特莉厲聲說道。「妳想聽聽看嗎?」
華特莉感到怒不可遏。她唸誦了一首她在兩年前才剛寫好的詩,一邊享受著那些尖刻的措詞。
「他們披著東方的闇影前來
為了尋找一件失落的珍寶
帶刺的薔薇、乾涸的血液在國境之南抹上『艾唐托』這個污漬
一群啜飲生命者,姓名啖噬者。」
安戈斯憤怒且不耐煩地顫抖著。「我們沒時間閒聊了,華特莉。我們需要奪取永生聖陽好讓我們能夠離開。」
依蓮達完全不理會安戈斯。她的平靜氛圍已被潛藏的怒意取代。她顯然變得緊繃,她的金色雙眼不停來回看著華特莉與安戈斯。「暮影軍團為何前來此地?」
華特莉尖刻地說出她的話。「為了奪走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不然妳認為他們是為了什麼來到這裡?」
「為了取回屬於我們的那樣東西,」依蓮達以一種慎重卻又憤怒的語調回覆道。「並且不打擾其他一切事物。那是我們最為神聖的任務。」
安戈斯咆哮著。「妳應該那樣告訴妳其餘的朋友們。華特莉,我們走吧。」
華特莉無視於安戈斯並緊握住她的刀。聖依蓮達宛如叢林貓般緊繃地站著,彷彿她可能在任何時刻以流暢的優雅和如短刀般鋒利的爪子攻擊。
這個吸血鬼露出了她的牙齒。「我將這份儀式的知識留給教會以擔起我的職責,而他們卻利用它成為入侵者?」
華特莉怒目而視。「他們應該要怎麼使用妳的贈禮?」
「他們應該要習得謙遜。」
華特莉極為驚訝。暮影軍團?謙遜?
「他們應該要為我們所有人尋找救贖,」依蓮達持續說道。「我了解我必須教導他們那些已被他們遺忘的事。」
依蓮達挺直身體,一道龐大的闇影掠過她的臉龐。她往前踏出步伐,經過華特莉與安戈斯身旁,並且消逝在空氣中一道陰暗的縫隙裡。
過了一會兒,陽光再現,琥珀色的斑白光線穿透上方的樹葉,而吸血鬼則消失了。
華特莉眨了眨眼,不停尋找她離去的方位。「噢,得了吧!」她嘆了一口氣,十分惱火。
「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嗎?!」安戈斯不悅地嘶吼著並用他的其中一條鐵鍊揮打鄰近的樹。它因這份衝擊而裂開並砸向地面,數十隻小動物與昆蟲則隨之慌亂逃竄。
華特莉怒視著牛頭怪。「你這是幹嘛?!你會讓別人發現我們!」
「妳太容易分心了!跟那個吸血鬼講話浪費了我們不少時間!」
「她是個活生生的聖人而且我想要對她說出心裡的感受啊!」
「妳那交換故事的行徑並不值得我浪費更多時間!」
安戈斯把一條鎖鏈朝華特莉的臉拋來,她勉強躲開了,它的熱度燒灼了她的臉頰。
儘管她的反應速度與訓練使她能夠往後翻,穩住身體,並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抽出她的刀,但等到她能夠將注意力集中在安戈斯身上並進行反擊時,他早已轉身朝歐拉茲卡尖塔跑了一大段距離。
安戈斯(粗魯、無法矯正、令人沮喪的安戈斯)即將比她先到達那裡。
而且華特莉不允許這件事發生。
傑斯
傑斯的內心已被情緒淹沒,被令人窒息的力量擠壓著,被固定在一條線上,在風中感到恍惚。甚至連精疲力竭也不足以形容他感受到的疲憊程度。
他從容不迫地反覆踏出雙腳登上歐拉茲卡的階梯,一方面又過度在意著跟在他身後的瓦絲卡。傑斯太過疲倦,沒力氣為了無法自制而感到羞愧。身體的病痛顯化為一陣陣失控的發燒。而一位通念師的心靈病痛只可能顯化為 . . .那個。一場驅除。一陣猛烈傾洩的心靈魔法。
他大部分的思緒正激烈地將仍持續湧入的記憶洪流分類與解析。現在他的心靈之井已深不見底,而其質地就跟他周遭世界裡的一樣五花八門且無窮無盡。他得專注於某個東西上。如果不這麼做,他確信自己將會再次被哀傷吞沒。
(一段記憶閃現:十二歲的他,坐在他臥室的角落,裹著一張羊毛毯,在家庭寵物死後抹去了一滴淚水。)
記憶持續湧入,但他現在已能夠控制它們。不再有心靈溢漏了。不會再讓瓦絲卡看見任何東西(謝天謝地)。讓她看見這麼多回憶令他感到尷尬,不過他也帶著逐漸增長的慰藉明白了她能夠產生如此多的共鳴。
畢竟,她也曾被虐待過。她知道。
傑斯欣喜於能夠擁有一段重複放空的時刻好讓他專注於進行心靈重組。一步接著一步接著一步地登向黃金城。左腳。右腳。左腳。
漫長的純金階梯沿著新露出的岩床側邊往上爬,不停地來回蜿蜒直到其表面。傑斯往上攀爬而瓦絲卡緊跟在後,同時他能夠看見粗厚的黃金礦脈在岩石中閃閃發光。隨著他踏出的每一步,他感到愈來愈彆扭,就好像每一步都等同於他用一個陌生人的珍寶來擦腳一樣。黃金既可塑又柔軟,他納悶著這座城市是否擁有某種方法來神奇地抵抗幾世紀的磨損。
這個關於黃金的念頭帶回了等著被揭露的可怕回憶的模糊暗示。
(黃金鱗片。砂岩。高溫。在他嘴唇與眼睛和喉嚨裡的粗糙沙礫。殘破、挫敗的朋友們。他正試圖要闖入一隻龍的心靈。感應那條龍的計畫內容,阻止他造成傷害,而且有那麼短暫地一刻,他成功了,他看見了目的,那場終局-)
那段記憶比較難以分析。傑斯試著看自己能否想起細節。
(巨龍發現了他的存在,並試圖透過讀取他自己的心靈來報復他。不過當這隻龍試著要闖入時,某個東西介入了,然後是一片黑暗。)
運氣不好。傑斯皺眉,感到沮喪。他想要記起之間的零碎片段。他想知道那條金色巨龍的名字。他渴望將它拼湊在一起好讓一切都變得合理。
但想到這隻龍卻讓他想起了另一隻。
(烏金在一座巨大的洞窟內展開身體。「祝你好運,傑斯貝連,」他如此道別,一邊將他那巨大的銀色尾巴纏在自己身上。)
傑斯眨了眨眼。烏金。他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個名字,但這份記憶的質地卻有些怪異。他在心靈中摸索尋找這段對話並且翻弄它的外緣,檢視它的側面,就跟多年前阿哈瑪瑞特干擾他的記憶時一樣謹慎小心。永遠不要相信關於任何比你古老事物的記憶。傑斯愁苦地明白了如果他沒想起曾學到這個痛苦的教訓,那麼他永遠也不會想到要加以探查。
就在那裡。一觸即發的裝置。一條等著被絆到的線,一種聰明又使人混淆的心靈魔法,一定是靈龍趁他沒注意的時候植入的。留下的咒語是一道簡單的指令。如果有人試圖讀取我的心靈並找到這段與烏金的會面,這段記憶將會被屏蔽,而且我將會被強制瞬間穿越時空離去。來到這裡。來到依夏蘭。
傑斯開始擔心。為什麼烏金需要隱藏我關於他的記憶?為什麼偏偏要命令我來到這裡?難道我是個誘餌嗎?
. . .而且在他清除我的心靈之前,我到底在那條金色巨龍的心靈裡發現了什麼?
他把關於靈龍與金龍的記憶都放到一旁,並決定等時間允許的時候再來思考它們。
他和瓦絲卡來到階梯頂端,因看似無止盡攀爬所耗費的力氣使他們的大腿酸痛並且心跳加劇。瓦絲卡伸展了她的大腿後肌,同時緊抓著一根黃金廊柱作為支撐。
他們站在一個巨大廣場的邊緣,而另一端則有一座高大的塔。他們四周都被一個接一個的黃金通道包圍,宛如一座耀眼的迷宮。
「如果我們從其他任何一處進來的話,我們就會被困在那裡面,」她說,一邊從瓶子裡喝了一大口水。「多虧你摔下那座瀑布。」
「不客氣,」傑斯平淡地回覆著。「如果需要我把自己拋下另一座瀑布的話再跟我說。」
一座中央尖塔霸佔了他們的視野。瓦絲卡掏出奇術羅盤。它正筆直地直向前方。她收起羅盤並看著傑斯。「我們需要的東西就在那裡面。你能否送出一道幻影好讓船員們知道我們的位置?」
傑斯沒在聽。一種心靈的存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把頭傾向這道心靈雜音傳來的方向。
「那是什麼?」瓦絲卡低聲說道。
「它很龐大。」
傑斯朝他們兩人上方送出一波幻影浪潮。它現在很輕易地便出現,不知何故甚至比他來到依夏蘭之前更容易。
(另一段記憶:花了無數小時背誦條文與技術,青少年時期的他在床上熬夜點燈研讀。外面傳來一座法師環塔的嗡響聲。米勒程序。間接操縱法。查西恩定律。不停反覆直到這些心靈策略的名稱、技術以及執行方式如同呼吸般輕易地出現。)
瓦絲卡望向他們才剛攀爬過的階梯並倒抽了一口氣。
一顆碩大無比的恐龍頭顱聳現於黃金城上方。

牠展翅高飛。每一次拍擊翅膀都讓樹林沙沙作響,而傑斯則因如此巨大的生物能夠飛翔而感到不可思議。這隻生物向上飛升,準備掠奪並處於警戒狀態,不過傑斯卻仍靜止不動。他和瓦絲卡在他的幻影之下非常安全。
在那一刻,傑斯注意到發生於他內在的變化。那個贊迪卡與依尼翠和拉尼卡的傑斯具有一種緊張的能量,持續感到無趣又悲慘地內向,總是不斷地意識到位於他心靈邊界上的缺損記憶的裂隙。而那個沒有過去的傑斯則在此地,警戒機敏,無論是何種情況都能感到自在並且準備好面對即將來臨之物。他想起了身為兩種傑斯的感受,但卻承認身為後者的感覺更加自然。在一瞬間,傑斯被自己嚇了一跳,然後明白了他近期在依夏蘭的真誠,絕非憑空捏造,況且他並不只有在失憶狀態下才能觸及心念。那就是一直以來的他。他只是忘記了。
(一段記憶:他的母親,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後返家,穿著她的治療師罩衫,雙手捧著一杯咖啡並在疲憊的臉上掛著一道淺笑,同時從敞開的窗眺望著遠方的一場風暴。他聽見粗大的雨滴使錫製屋頂答答作響。空氣聞起來就像是潮溼的水泥與家園。)
傑斯露出笑容。他很高興能夠記起他的母親。
我希望她還活著,他在心裡想著。
「牠離開了,」瓦絲卡說,打破了這道咒語。
傑斯想起了自己身在何處並終止了他的幻影。
「我從沒見過你如此迅速地施放那道幻影,」她說。
傑斯帶著緊繃的笑容點了點頭。「現在,我能夠想起我的導師教過我的技巧了。當我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比我自學的還多。」
「所以青少年的你比起成年的你擁有更精鍊的技術囉?」
「而現在的我卻同時具有兩者的知識。這好...奇怪。」
瓦絲卡直視著他的眼睛。「你很不可思議。你知道這點,對吧?」
傑斯也向她報以微笑並感覺到臉頰一陣溫熱。「我只是盡力而為。」
「那麼,你的盡力相當不可思議,」瓦絲卡說,一邊轉向中央尖塔並走近一扇看似位於尖塔背側的巨大門扉。
莉蓮娜從未告訴過傑斯他很不可思議。
莉蓮娜會嘲弄。她會開個輕蔑的玩笑,翻個白眼,然後說他愛炫耀自己。她會有好幾天都不願浪費時間與他交談。她會用一隻鱷魚的嘴吞噬一隻惡魔,她的大笑聲蓋過了牠血肉支離破碎的聲響。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卻從未說過他不可思議。
傑斯趕上了開始行走的瓦絲卡,接著他們便一同走向中央尖塔。她掏出奇術羅盤-它的指針正筆直地指著他們眼前尖塔的後門。
上方的天空轉為一片驚人的漆黑,更有煙霧繚繞於他們上方的塔頂周圍。傑斯與瓦絲卡彼此交換了擔憂的眼神。
「難道那群吸血鬼已經先抵達這裡了?」瓦絲卡問道。
上方那不停翻騰的漆黑雲霧已給了他們答案。
瓦絲卡試著要把門推開,但它卻被緊緊地鎖上。她往後退並仔細看著大門正面的圖案。
「那是個迷宮,」瓦絲卡與傑斯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短暫且尷尬地互看了一眼。
瓦絲卡朝傑斯比了個手勢。「開始吧,」她說。「你是迷宮達人。」
傑斯開始勾勒出這面迷宮的解答,一道藍色的魔法線條正跟著他的手指移動。在天空中翻騰的黑霧驅使他加緊速度。
「正是在下,」他興味盎然地說。「傑斯貝連:現世十會盟,通念師,幻視師,迷宮達人。」
「還真順口啊。」

他的手指來到位於門中央的迷宮終點。傑斯感到異常緊張。他探出感官以感應門的另一側有什麼人,並且在他自己和瓦絲卡周圍豎起一座心靈護盾。
「怎麼了?」她問道。傑斯這才發現自己竟驚訝地合不攏嘴。他指向了門上的符號。
「那就是每當我們試著要穿梭時空時就會出現在我們頭頂上的符號,」他說。「那是俄佐立的符號。」
瓦絲卡皺起眉頭。「俄佐立在拉尼卡。」
傑斯感到胃部一陣翻攪。經過短暫的心靈掃描後,他感應到房間裡有人。他帶著些微驚慌的表情看著瓦絲卡。「有任何著名的俄佐立鵬洛客嗎?」
瓦絲卡眉頭深鎖。「我不知道。根本沒有這樣的索引。」
「那一定得是某個在組織裡位高權重的人。某個將該符號視為他們自我身分認同的人,」他說,一邊指著他們面前的門以強調他的陳述。
「俄佐立的元祖公會長是俄佐。」
傑斯再次審視這個房間並且呆住了。他不知道是誰在裡面,但他立刻就知道是什麼東西在裡面。這個人的心靈感覺非常熟悉,如迷宮般曲折,他之前只遇過一個類似這樣的心靈。
難道俄佐是一個史芬斯?他以低聲的恐懼在瓦絲卡的心靈中詢問著。
她擔憂地回看著他。她知道史芬斯對他有什麼意義。她用手指輕拍她的頭部側邊,接著傑斯便在心靈中聆聽著。
你不會再被史芬斯傷害了,她堅決地說道。她的眼中暗示著一道殘忍的琥珀色閃光。
傑斯原本可以當場擁抱她。但他想起了她的習慣,於是便改為一道感激的微笑。
我會開始為石化術充能,瓦絲卡說。只要你下令,他必死無疑。
傑斯點了點頭。焦慮正在啃食他的神經,他的嘴裡都是沉悶恐懼的金屬味道。
他推門並看著它嘎吱一聲地打開,在展現內部房間的同時一邊篩落了灰塵。
這個長形的房間爬滿了藤蔓。遠端有一個巨大的王座,而一個龐大的發光圓盤則被嵌在天花板上。乾草與布匹四散於王座的基部,而就在傑斯與瓦絲卡打開門的同時,他們看見一個巨大的形體抬起了他那長了鬍鬚的頭。

「來者何人?」史芬斯說道。他的聲音因久未使用而變得粗啞,更像是動物的嚎吼而非人類的言語。
瓦絲卡向前一步,充滿自信又冷靜,完全展現了身為船長的風範。「兩個來到這個世界的陌生人。報上你的姓名,別擋我們的路,而且如果你不想死的話就交出永生聖陽。」
史芬斯怒視著他們兩人。他非常龐大,帶有一種掠食者的張力,與他眼裡透出的智慧形成強烈的對比。
「我是俄佐,律法使者,」他咆哮著,一邊歪著頭凝視瓦絲卡。「而且妳將會在這輩子裡第三度成為囚犯,蛇髮妖。」
傑斯急忙在史芬斯與瓦絲卡之間建立一道心靈守護。她早已因史芬斯的心靈入侵而驚訝地呆立原地,因他不假思索便潛入她的心靈而震驚不已。
他實在太像阿哈瑪瑞特了,傑斯想著,他的胸口因回憶而逐漸緊繃。他收起他的恐懼。他不受史芬斯支配。不再是了。
「你要稱她為船長,」傑斯以謹慎的語調說道。
史芬斯大聲咆哮並將視線越過瓦絲卡看著傑斯。「那麼你又是什麼角色?」
「我是傑斯貝連,現世十會盟,」他滿懷自信地說。
史芬斯縮起了翅膀。「那個保險裝置?!」
「是海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