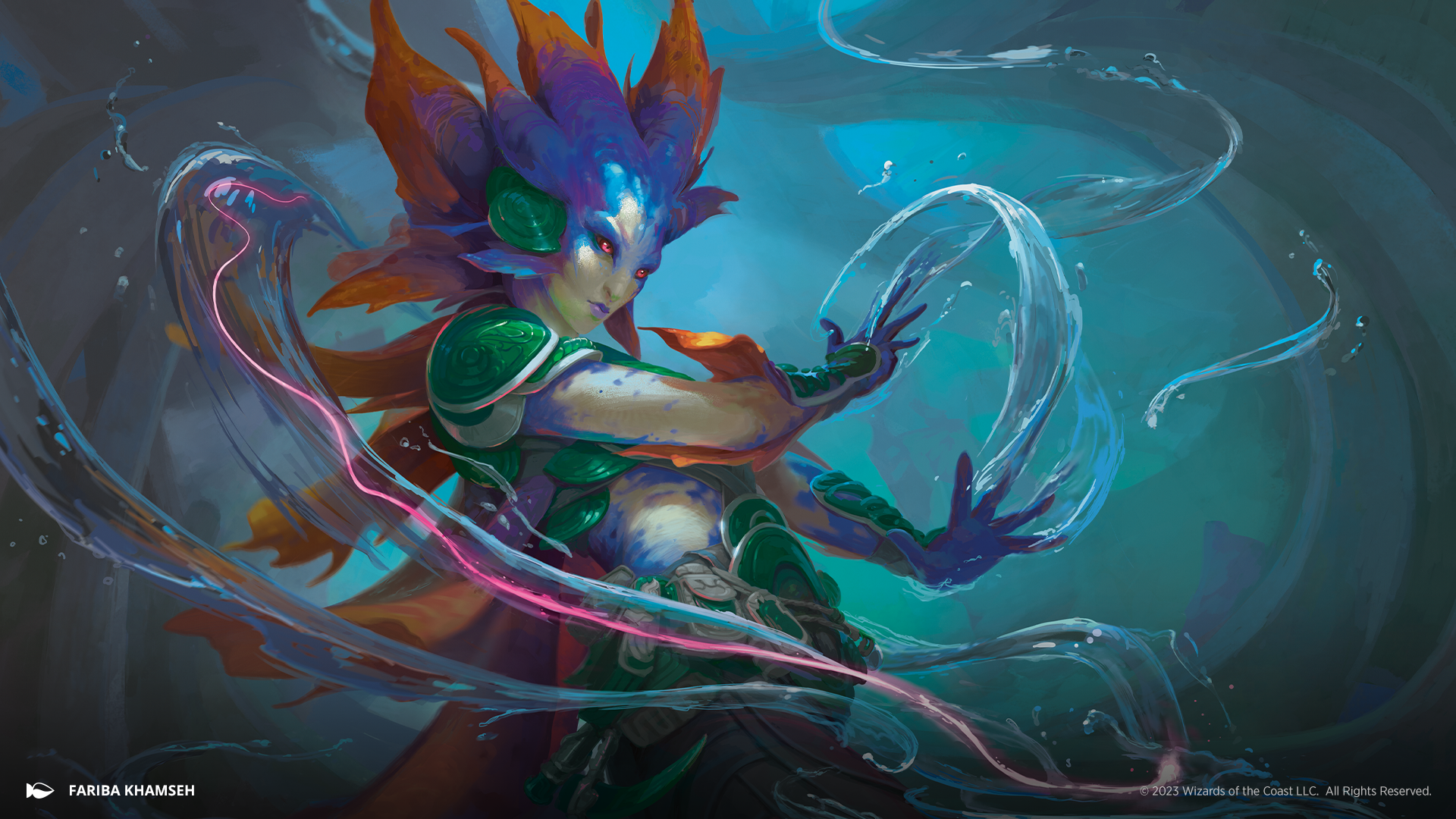依夏蘭迷窟|第三集
薇塔
如果幾天前有人對薇塔說她和一位象族考古學家將會穿越地底遺跡追逐一個鬼魂,她會叫他們去看治療師。她也會詢問象族是什麼東西?
這個鬼魂-他自稱阿布羅-飄浮而非奔跑,隨著他高速穿梭於建築之間,他的斗篷也在一陣無形的微風中不停拍打著。昆特在他身後奔馳,捲起象鼻以免礙事,而薇塔則緊追在後,一邊檢視潛藏於周遭環境中的危險。
很可惜,殿後就表示她最後才看見有什麼東西在繞過轉角後的地下河流旁等待他們。
「泰坦!」阿布羅大喊,然後消失在一團盤繞的紫紅色能量中。薇塔滑行至停下,幾乎撞上昆特的背。
一個龐大的形體隱約地出現在前方,少說也有她的兩倍身高。她或許把它誤認為生長於牆上的真菌的一部分,直到它開始移動。它的頭部是一個層狀的巨型蘑菇,就像那些生長於叢林樹上的,而它的肩膀與胸口則長了一簇簇小型的圓頂羊肚箘。許多參差不齊的硬殼尖棘突出於它巨大的手背上,並沿著前臂生長。
一道低沉、不協調的嗡響聲-比起聽見更像是看見-使微塔手臂上的汗毛直豎。就在她或昆特能做出比直盯著看更多的反應之前,那隻生物已朝他們衝鋒而來。
「後退,」薇塔告訴昆特。她揮舞她的劍以吸引那隻生物的注意,一邊繞著圈奔向湍急的河流並遠離昆特。蒂洛納理,重擊我的敵人吧,她祈禱著。
泰坦抓起半座頹圮的牆並將它扔向薇塔。她跳向一旁,那塊巨石飛過她身邊並砸碎在她後方。它的衝擊使鵝卵石和碎片飛濺,劃破了她露出的肌膚並從她的鎧甲上彈開。
發出一聲嘶吼,泰坦轟隆地衝向她並仰身準備揮擊。薇塔彎身閃躲,衝到一條如樹幹般粗大的手臂底下。她翻滾至蹲姿並且劃傷它的小腿肚,然後突然跳起身。一個人類會失去行動能力;泰坦卻不受影響。它轉身再次揮打,薇塔再度滑到它的兩腿之間,朝它的後方衝刺。她用劍劈砍,削出一團纖維物質卻毫無作用。她還不如跟一株落羽杉打鬥。
一隻矛尖刺穿了泰坦胸口。華特莉、因提、卡帕羅提,以及其他戰士們已於薇塔戰鬥時抵達,而且他們齊聲嘶喊並發動攻擊。他們包圍這隻生物,嘲弄它,戳刺它,同時削去一些部位直到蘑菇與硬殼樹皮散落於地。為了恐龍群的自身安危,牠們被隔離開來,但潘塔札卻跳上去以腳上的尖爪抓耙,在它的背上留下長條痕跡。
他們戰鬥得愈久,薇塔的肌肉就愈疲勞,她那不平整的呼吸在肺臟裡燃燒著。他們的揮砍無法減緩泰坦的攻勢,而且它沒有展現任何感到疼痛的跡象。它撞開他們的長矛,用巨大的手抓住他們的劍並將它們扔進廢墟。它的傷口緩緩流出黑色液體,形成黏稠的絲線並且彼此交纏,直到它們固化並長出新的真菌。它把長矛從自己的胸口抽出並用來揮打其中一位戰士。武器沒擊中,但泰坦的尖棘手臂卻有如劍龍尾巴般地砸中她,使她被拋飛撞上牆。她癱倒著一動也不動。更多漆黑物質從這隻生物口中灑出,而且它吐向一位鄰近的戰士;他大聲嘶喊,同時焦油般的物質腐蝕穿透了他的鎧甲。薇塔跑到他身邊想幫忙,但這名男子殘骸中的血跡白骨景象卻告訴她已經太遲了。
薇塔稍後會替亡者的靈魂祈禱。但此刻,她會戰鬥。
「有更多敵人出現!」昆特大喊,一邊指向城市深處。
十二隻新生物包圍了他們,它們跨越鄰近河流上的崩塌橋樑,爬過荒廢的道路並且攀越半倒塌的牆壁。小型版本的泰坦,由各式各樣的蘑菇組成。有些配戴著粗糙的武器,很可能是取自這個空曠地方裡的眾多屍體。
烈陽帝國的戰士此時以寡擊眾並且遭受夾擊。其中一隻沒有武器的生物從自己身上摘下一顆蘑菇並把它丟在另一名戰士腳邊。蘑菇發出神秘的綠光,噴出濃密的黑黴包覆了男子的靴子並擴散至他的雙腿。他踉蹌了一下,接著黑黴湧入他口中。
薇塔的心臟一陣緊繃,因為她突然明白自己會在這個地方倒下,永遠再也見不到三相烈陽的光芒。
接下來,戰局改變。
一陣浪潮自地下河流湧出,撞開了其中兩隻生物。沒多久,有六名川流使跳到岸上,帶著玉矛、玉劍與魔法加入戰鬥。
「這場仗已經輸了,」其中一位川流使說。「跟我們一起前往安全之處吧。」
薇塔猶豫了。在大戰前經歷過於歐拉茲卡發生的事,烈陽帝國與川流使之間的關係一直都相當緊張,甚至敵對。他們能信任這些人嗎?
得從某處開始信任。或許就從這裡開始。
薇塔尋找昆特的身影,發現他正在附近的一座牆後方施放一道咒語。一件遠古武器從地面升起,彷彿被一個精靈所操控,在半空中不停旋轉並埋進一隻蘑菇生物的脖子。
「昆特,我們走吧!」薇塔大喊。他立刻聽從,於是她便替他們清出一條通往河流的路。
其中一位川流使注意到他們並握住她空出來的手。他們喃喃唸誦咒文,一邊繞著她的臉部移動手指。突然間,空氣的味道不一樣了,充滿濃郁的濕氣。一道彩虹光澤覆蓋了薇塔,彷彿她被包覆在一個依照她的外型塑造的氣泡中,接著她戳了一下自己的手臂,沒感到什麼不尋常之處。
「祝旅途迅捷,小姐妹,」人魚說道,接著把她推入河中。
馬科姆
升降梯逐漸深入岩洞井,纜繩嘎吱作響,木頭支架不停擺盪。馬科姆用眼角的餘光看著他受傷的同伴,同時內心浮現一陣冰冷的恐懼感。布里奇看似安然無恙,還有那些沒有一同探索駭人恐龍洞穴的成員,但至於其他人 …他們不太對勁。
他們傷口上的黑色印記已經擴散,沿著任何裸露的皮膚形成精緻的圓環與線條。更糟的是,它們已開始發出一種噁心的綠光。海盜們沒有抱怨疼痛或不適,畢竟他們通常會不停抱怨並要求休息。他們反而一會兒恍惚疏離,一會兒又帶著怪異的興致查看他們的周遭。
在他的肩燈照明下,岩洞井的牆面投映出潮濕的光芒,覆蓋著以駭人的步調擴散的黏滑真菌叢。洞穴未曾完整乾燥過,但這個卻太過分了。隨著腐爛與黴菌的氣味加重,馬科姆從他的背包裡抽出一塊布繫在臉上,蓋住了他的口鼻。布里奇模仿他,而馬科姆也差點對他們的滑稽樣貌哈哈大笑。就像一般的竊賊或土匪,而非海盜。
並不是說他最近有從事許多海盜活動。而是莽霸聯盟讓他一直忙不過來。
升降梯在撞上某個東西時突然搖晃了一下。其中一名海盜探出護欄外緣查看。
「看來是一顆大蘑菇,」她說。
「妳能夠切開它嗎?」馬科姆問道。
她點了點頭,抽出了她的劍。在揮砍它幾下後,升降梯移動了。這位海盜打了個噴嚏並往後踉蹌。
「好噁心,」她說。「它像麵粉一樣爆開。」她一邊咳嗽一邊揉眼睛,同時另一位海盜則捶打她的背。
在她站立之處,有一團閃爍的綠色孢子於靜止的空氣中升起,如煙霧般逐漸變濃。馬科姆瞇起了眼睛往後退。他看了一眼那些受傷的海盜們,正 面無表情地站在升降梯中央,他們的傷口也閃耀著相同的顏色。有某種關聯嗎?
彷彿做出回應,那些海盜衝向兩名未受傷的海盜並將他們推進那團發光的孢子雲中。驚訝的叫喊聲轉為濕咳,然後窒息與乾嘔,漆黑的液體濺灑於地板上。

就跟開始時一樣,這場疾病突襲也迅速地終止。被影響的海盜們抽搐地起身並面向其他人。他們的眼睛是呆滯的綠色,多條黑色血管在他們的臉上延伸。空氣從他們口中嘶嘶地傳出,就像有漏洞的橡膠氣囊。馬科姆抽出劍並往後退開,一邊調整那條還蓋住他口鼻的頭巾。在他們被感染的伙伴發動攻擊之前,存活的海盜剛好有足夠的時間抽出他們自己的武器。狹小的空間使他們幾乎無法進行閃躲;每一道揮砍或戳刺都可能傷到朋友而非敵人。
「大爆炸嗎?」布里奇說。
「不行!你會害死我們所有人,」馬科姆大喊。
他翻越護欄,缺少氣流迫使他必須靠自己的魔法飛行。他繞回來緊抓著升降梯繩索,同時它將他往上拉離。在他下方,海盜們死命地打鬥,但就像洞窟內的恐龍,這些感染者看似對疼痛或傷害無動於衷。
隨著升降梯持續下降,布里奇也來到繩索上的馬科姆身邊。「逃離嗎?」布里奇喊道。
一聽見他的聲音,感染者們同時以他們的邪惡綠眼仰頭看。
「切斷繩索,」馬科姆說道,他的血液變得冰冷。「快點。」
布里奇用他的雙腳和尾巴抓住繩索。他用刀子切一條纜繩,而馬科姆則割另一條。為了承載一定的重量,繩索相當粗厚,而當感染者開始沿著升降梯側面往上爬時,他們還割開不到一半。
雖然馬科姆的肌肉在燃燒,但他卻割得比較快。他手中的纜繩逐漸解開變細,接著突然斷裂,其力道使他鬆開了手。升降梯劇烈晃動,裡面的海盜感染者跌得東倒西歪。布里奇在他的繩索斷裂時嚴肅地緊抓著,伴隨著一陣可怕的寂靜,升降梯墜入了黑暗中。
閉起眼睛,馬科姆試圖讓那顆如蜂鳥般顫動的心臟平靜下來。「來吧,」他終於開口。「我們不能待在這裡。」
他交替著飛行與攀爬,而布里奇則在繩索上跟著他行進。他仔細地避開鄰近牆壁上的一叢真菌捲鬚,並渾身顫抖著發現一個怪異的眼狀蘑菇看似要跟蹤他們的行動。馬科姆原本會認為它是他憑空想像之物。
現在,他納悶是什麼可怕的生物能把海盜和恐龍轉變成失魂傀儡-而且又是為什麼。
巴洛梅
跟一座燃燒熔岩瀑布一樣令人不悅,多個像這樣的噴口-甚至是這類河流-更是無限糟。若通往阿洛佐茲的路途要持續穿越如此險惡又致命的地形,巴洛梅思索著-儘管維托堅持己見-一個像這樣強大的神是否應該被找到。
追逐那位怪異新成員凱瀾且形似鬼怪的生物並沒有再出現。即便如此,隨著他們的朝聖之旅逐漸深入地底,他們就發現更多居住的跡象:鑿進峭壁與鐘乳石的建築,被陌生雕符覆蓋的發光印記,生長於砂土中的蒼白無葉植物花園。他們從未遇見任何居民,但疾行聲與細微動靜則暗示了他們並不孤單。
阿瑪利亞與凱瀾交談,而他則帶著驚喜與不自在的情緒檢視他們周遭環境。巴洛梅在這位年輕製圖師身上看見女兒的影子;儘管在近期入侵行動的貧乏資源中存活下來,但她卻依然如此天真無邪。為了保護那份純真,為了守護像她這樣的人的未來,他將做出任何必要的犧牲。
到目前為止,那表示屈從於維托的命令。當米拉達女王指派巴洛梅加入這個探險隊時,他被告知要假意順從並發掘維托真正的意圖與忠誠度。他當時沒意識到這位法皇的想法已轉為異端,他早已背離教會。他也一直無法找出是誰把聖塔理安的長槍與日誌交給維托,但這暗示了女王的對手-支持伊埃多的沃娜以及其他所謂先知的陣營-比他們所期望的更龐大且團結。
要是阿洛佐茲本尊也支持安提費克斯呢?巴洛梅一想到這個就渾身顫抖。
軍團進入一座遼闊、平坦的高地,這裡俯瞰著一雙熔岩瀑布。轉眼間,寂靜就轉為叫喊與動作的嘈雜聲響。克萊維諾的士兵們以防衛姿態圍住其他人,同時抽出了武器。
有二十四名戰士包圍了他們,比吸血鬼高大,魁梧,擁有大貓的臉孔以及相稱的斑點皮毛。他們戴著精心裝飾的頭盔與鎧甲,並拿著弓和看似惡毒的鋸齒狀黑曜石刀刃與長槍。露出的獠牙應允暴力,巴洛梅並不想測試他們使用武器的技巧。他們那一方有數目上的優勢,除非有人算上軍團的搬運工與囚犯。

「你們要跟我們走,」其中一位貓人說道,一邊揮舞著一支佈滿雕符的長槍。
「你是誰?」維托問道,他的聲音裡透出冰冷的權威。
「我是庫琪,豹族鬥士,」便是回應。「你們要跟我們走,不然就受死。」
巴洛梅清了清喉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神聖的朝聖之旅,」他說。「我們只求安全地通過這些土地。我們無意造成傷害。」
維托的怒目暗示了他若非厭惡巴洛梅的干涉,就是討厭他的謊言。
庫琪轉移她的視線,同時傾斜了頭。「你們的任務與我們無關。豹王歐奇尼亞豪將會決定你們的命運。」
克萊維諾看向維托。「要下令嗎?」
「我們早已經歷太多打鬥,」巴洛梅悄悄告訴維托。「士氣與補給皆低落。外交手段可能比樹敵對我們更有利。」
維托把注意力轉向庫琪。「我會去見你們的豹王,」他說。「帶路吧。」
豹族戰士們將武器指向軍團成員。庫琪用她的長槍示意他們跟隨。
維托靠向巴洛梅。「不要再破壞我的計畫,」他悄悄說著,他的聲音充滿了威嚇。
巴洛梅點頭表示認可。
他們跟著庫琪越過更多石橋,深入這些豹族的城市。既然他們被護送前行,這些住所的居民也現身,還有一些怪異、蒼白的鬼怪。有一整個文明存在於這些洞穴與隧道中並且從未前往地表與人接觸,這令巴洛梅感到驚奇不已。
或許像他們過去那樣打開大門將會有某些收獲。或者,鑑於這些人生性多疑,也可能一無所獲。
庫琪讓隊伍停下。「瞧,」她說。「從歐爾特克人的時代起,你們是第一批見證斑科杰的人。」
巴洛梅往後退,同時敬畏地以一隻手捂住嘴。跟此景相較之下,他們在幾小時前經過的幾間小屋根本不值一提。一整座城市-隨便就是奧塔圖瑞琮的規模-被建造於鐘乳石群內,如此龐大就像是顛倒的山脈。有些建築看似直接由粗糙的岩石削切而成,而其他建築則具有宛如陶器般被漆成白色的牆壁。繩橋與網子延展於建築之間,還有吊著奇特車廂的粗纜繩,它們的輪子位於頂部好讓它們能前後移動。乘客乘坐於內,爬出車廂與其他豹族一同沿著那令人不安的懸空街道行走。
隨著豹族把軍團成員分成兩群以便往上運輸進入城市,巴洛梅也把他的緊張藏於平靜的外表之下。如果外交手段失敗了,他們幾乎不可能逃離這個地方。有些身為天行客的士兵能飛行,至於其他人 …他的視線飄向阿瑪利亞,她正站在凱瀾身邊,於劍柄附近抽動的手指透露了她的焦慮。
豹族戰士持續看守他們跨步越過一座寬闊的石橋前往最大的鐘乳石群。不像其他地方,這個鐘乳石外部並沒有鑿出任何建築,甚至連窗戶都沒有。反而有數百個雕符覆蓋了每一處可見的表面,斷斷續續地發著光。
他們穿過位於石橋末端的一個巨大開口,其中央還有一座旋轉門。有更多守衛在他們經過的同時立正站好,就跟那些形似他們的潛行掠奪者一樣安靜。其中一名軍團搬運工靠得太近了,於是鄰近的守衛便出聲咆哮。
鐘乳石內部被一座巨大的石雕金字塔填滿,數百級階梯通往位於頂部的小房間。有一種奇怪的雜音迴盪在這個洞穴空間內,其來源不明。
謝天謝地,他們沒有被迫登上階梯,反而被帶往金字塔內的一個長形房間。其兩側各有一排雕柱,而豹族則蹲踞於中間的織墊上。他們那精緻的頭飾與頸環暗示了某種形式的貴族或僧侶身份,而且他們全都注視著軍團成員經過,有些還露出讓吸血鬼之牙相形見絀的獠牙。
坐在房間末端高台的王座上,一位全副武裝的高大豹族正漫不經心地玩弄著一把鋸齒狀巨劍。這位大概就是豹王歐奇尼亞豪。
「妳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庫琪?」他問道。
庫琪在說話時恭敬地露出她的脖子。「來自地表的入侵者,豹王,」她回覆道。
「我們只是路過,」維托說道,一邊禮貌地鞠躬。
「有人問你話時才能說話,」庫琪咆哮道,同時將她的長槍指向維托。擺出輕蔑的表情,維托不理會她。
豹王歐奇尼亞豪好奇地看著維托。「你來我的王國有什麼目的?」
「我們是朝聖客,」維托回應。「我們正在旅行前往我們的神-阿洛佐茲-的領地。」
「除了我以外這裡沒有其他神,」歐奇尼亞豪握住他的劍說道。「波克,」他說,同時看往他右側一群穿著長袍的參謀。一位擁有黃褐色皮毛的壯碩豹族往前站了一步,他的雙臂交疊於身後。他穿著一件簡單的銀質挽具,上面蝕刻著豐富的雕符與象形文字。他的頭髮成辮垂下,髮尾還繫著閃爍的銀質小勛章。
「波克是我的神話織者,」歐奇尼亞豪說,一邊介紹這位豹族。「他會講述。用我們的文字,他會看透你們所有人。」
波克點了點頭。他把手臂舉到胸前並輕聲說出一個短詞。雨的氣味、暴烈閃電,以及乾燥夏日的熱氣皆充斥於空氣中。他的爪子之間升起盤旋的綠霧,凝聚為層層堆疊的形體,顯露出一個模糊卻可辨識的影像:
一張咆哮的臉,它露出獠牙並且持續增長。在它注意到周圍豹族的當下,臉孔扭曲,泛起波紋。尖嘯了一聲,它向前猛咬,宛如野獸咬住食物般地啃咬著神話織者波克。
神話織者波克垂下了手,取消這個影像。他望向歐奇尼亞豪,搖了搖頭,然後走回到參謀團的行列間。
歐奇尼亞豪站起身對聚集的豹族說話,就在軍團士兵上方交談。「一場侵略行動會招致另一場,」歐奇尼亞豪說。「我們不允許它發生。」
軍團士兵們轉為防禦姿態。巴洛梅把一隻手放在阿瑪利亞的手臂上,然後他們擔憂地互看一眼。
豹王歐奇尼亞豪比向坐下的群眾。「我判這些闖入者受沙池之刑。執行我的制裁。」
有些吸血鬼抽出他們的劍,而維托則將長槍瞄準了豹王。不過,就在他們能夠攻擊或自我防衛之前,他們兩側的豹族開始咆哮並舉起手臂。
閃耀的雕符燒灼了空氣,酷似豹族毛皮上的斑點。這道魔法竄出並宛如鎖鏈般地纏住軍團成員,迫使他們跪下。維托奮力掙扎,但他的長槍卻被無用地壓在他的胸口。他以惡毒的眼神瞪視巴洛梅,如果眼神可以殺人,那麼巴洛梅早就死了。
「這不公平!」凱瀾從群眾後方大喊。「我們什麼也沒做!」
豹王歐奇尼亞豪齜牙咧嘴。「火焰對公平不感興趣。它就只是燃燒。」
一個接著一個,戰士們把軍團成員帶往一座巨大的噴泉,頂端有一個豹頭。但從雕刻的口中流出的並不是水,而是沙子,聚積於下方並流入一個大洞裡。維托是隊伍裡第一個抵達這座建築的人,他的眼睛裡燃燒著憤怒。
「雖然我被敵人所困,」維托吟誦道,「我的神將會賜予我力量和復仇。履行祂的意志。」
巴洛梅看著豹族把他的同伴們丟進沙坑裡,有些人默默屈從,其他人則叫喊或打鬥。維托的頭部先進沙坑,束縛他的魔法鎖鏈依然將長槍緊緊固定在他身上。接下來是克萊維諾,不停嘶叫並露出他的獠牙。阿瑪利亞在下沉時保持不動並且出奇地冷靜;一開始是她的腿,接著她的手臂也消失於地表之下。她嘴裡喃喃唸著某些他無法光看嘴唇就讀出的字句,睜大了眼睛並失神地看著前方。她對面的凱瀾不停掙扎並揮打沙礫,隨著他逐漸滑近敞開的排沙口,臉上也明顯地露出了驚慌。
在阿瑪利亞消失之前,她對凱瀾說,「憋氣。」
難道她被賜予一場預視?巴洛梅希望是如此,否則他們的任務將結束,而且這都是他的錯。他跟隨她的引導並讓豹族用巨大的粗毛手臂將他舉起,然後在被粗暴地扔下噴泉坑的同時對抗自身的恐懼。當沙礫將他吞沒時,他唯一的慰藉就是維托將沒有機會在圖瑞琮興風作浪了。他只希望那份目標不需要付出如此高的代價。

薇塔
薇塔跌跌撞撞地穿過冰冷漆黑的河水。一道不可思議的疾速水流拉著她向前,固定於她腰帶上的三相烈陽光芒在她周圍投映出狂野陰影。她意識到自己可以呼吸,毫無疑問,這得感謝人魚施放的咒語。即便如此,她還是難以控制前進的方向,並且只能盡量不讓自己被沖向牆面或河床。
有時她會瞥見上方一座更寬闊的洞窟,或是下方宛如湖泊或岩洞井般敞開的地面。有時候一閃而過的綠光會戲弄她的視野邊緣,或者隧道分岔,而她會瞥見某些遙不可及的替代路徑。
自始至終,水流帶著她前往那未知的目的地。終於,經過了許久,遠方出現一道新的光芒。
伴隨著短暫增強的壓力,她衝入冰冷清澈的開放水域。薇塔踢腿朝水面游去,一邊搜尋其他人的身影,並發現他們早已游向最近的河岸,也包括那位把她推下水的斥侯。人魚守衛在附近徘徊,他們的鰭如波紋般擺盪,同時他們於原處上下浮動,看著她前進卻不打算幫助或阻礙她。很快地她便爬上岸,欣喜地看見她身旁的昆特早已坐起身並以明顯敬畏的神情看著他們四周。
一座巨大的石城從一片地下海洋-淡水,而非鹹水-中升起,甚至還往下延伸到更深處,以類似三相烈陽殿堂的方式聳立著。明亮的燈光燃燒於低層建築上方,而一長串生物冷光飾品與籃子則關著許多螢火蟲,照亮了可見的街道與小巷。她所見之處都有川流使在行走、潛游或休憩,同時謹慎地看著新訪客並彼此竊竊私語。
華特莉擰乾她的衣服,一邊探查這塊區域。「這裡肯定有上千名川流使,」她說。隨著潘塔札把自己甩乾並把水灑得到處都是,她也皺起臉。
那位年輕的人魚斥侯展開她的鰓。「我的母親說這是依夏蘭史上規模最龐大的人魚群落。」她朝薇塔伸出一隻手,而她也握住手並站起身。「我叫妮坎琪,」她說。「歡迎。」
華特莉眉頭深鎖。「如果容許我提問的話,你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在等待通往源頭的最終大門敞開,」妮坎琪說道,一邊比向位於殿堂階梯頂端的腐蝕大門。「我的母親-偉大的塑形師帕修娜-能夠告訴妳更多。她在繁根樹死亡後發現了這個地方。」
華特莉凝視著那扇門,瞇起眼睛彷彿要從遠處看得更清楚。「這會是瑪察欄蒂嗎?」她喃喃說道。「難道我們真的發現了-如那首詩所宣稱-通往人類誕生地與眾神家園的門嗎?」
「如果它是的話,」昆特說,「我想知道他們在這裡還發現了什麼。硬幣帝國有來到這麼遠的地方嗎,還是他們待在靠近地表之處?想像會有什麼重要的歷史神器潛藏於某些遠古壁櫥裡。」他檢查了卷軸上的緘印,明顯地對於一切完好無缺感到相當滿意。
薇塔帶著好奇心和些許不安看著他。「如果你找到神器的話,你會如何處理它們?」
「我想建立一座適當的挖掘場,」他說。「以確保一切事物都盡可能被謹慎對待。」
「然後呢?」薇塔問道。「你把東西挖出來後就把它們留在那裡?」
「不一定要把它們留在那裡,」昆特說。「我想那得看你們所有人想怎麼做。無論你們想把一切都留在這裡,或是把某些物品帶回歐拉茲卡,甚至可能建立一座博物館。」
「所以,人們會來這裡 …盯著東西看嗎?」薇塔皺眉。「好怪。」
昆特大笑。「我想那看起來確實很怪。那是確保過往的故事不會被遺忘的一種方法。」
「啊,就像戰士詩人,」薇塔說,同時看了華特莉一眼。
「對,沒錯!」昆特驚呼。「我會記下挖掘的過程,然後替我在阿凱維沃的同事寫一份詳細的解說,用以分享我們的發現。」他望向遠方。「或許我可以在多重宇宙各處出版它 …」
薇塔的眉頭皺得更深了。「但那不是你的故事。」
昆特稍微張開了耳朵。「這麼嘛,當然不是,我只是那個講述故事的人。」
「為什麼是你?」薇塔逼問。「你不是來自依夏蘭。你不屬於烈陽帝國,也不是川流使。你不該替我們講述我們的故事。」
「那麼,或許就不是講述了,」昆特說,一邊別過頭去眺望水面。「而是紀錄。傳播。妳知道的,我為此受過訓練,」他添加了些微怒意。「我不會踐踏你們的歷史。」他用象鼻把護目鏡從頭上拿下並開始用一塊布擦拭它。薇塔呼出一口氣,納悶自己為何會如此在意。為何這件事會令她感到煩惱。當然,她曾夢想著有一天能跟隨華特莉的榜樣並親自贏得戰士詩人的重任。但戰爭卻粉碎了那些夢想,就像他們在這些洞窟裡發現的陶器。她曾經是個軍人,也是個海盜,有時會幫莽霸聯盟偷竊並販賣不只來自圖瑞琮的神器,也包括她自己族人的文物。那些竊盜行徑替她賺得旅費也讓她不會挨餓,從未讓她感受過偶然的一絲內疚。她應該得到比軍隊裡更多的東西,不是嗎?不過她已拋下那一切。而現在的她是—什麼?一位探險家嗎?她能否也成為一位故事收藏家?收集那些來自她的故鄉,以及她的族人的故事?
於這場對話進行時,華特莉一直靜靜地坐在附近,而此時她向薇塔露出一道淺笑。「不是每個人都了解文字的力量,」她說。「以及它能夠對其他人造成的掌控。」她開始背誦一段薇塔不認得的詩。
當我的遺骨於大地中沉睡時,
誰將共享我的記憶?
友人可以豎立紀念碑
而敵人會褻瀆我的墳。
當他們也消亡後
他們的孩子將記得什麼?
「想到遺失了這麼多就令人難過,」薇塔喃喃說道,一邊仰頭看著遠處金字塔頂的那扇怪異的門。
華特莉友善地捏了一下她的肩膀。「不過,當找到遺失之物並分享這些事物時卻是如此喜悅。」
薇塔看了昆特一眼,然後看了因提和卡帕羅提,他們正在組織其他士兵並且悄悄地發號施令。或許讓某些東西埋藏起來比較好,端看人們打算如何處置它們。或許某些紀念碑應當被扳倒。
她希望無論通往所謂眾神家園的那扇神秘黃金門後面有什麼東西,那都是一份祝福而非詛咒。
馬科姆
馬科姆和布里奇停下來喘口氣的隧道聞起來既乾燥又無人使用,可能在礦脈耗竭後被遺棄,或是沒發現任何東西值得更近一步探勘。他和隧道的開創者都有這個共同點:他無意再繼續深入。他的肌肉疼痛,而且使用過多魔法也讓他的頭部抽痛。
市中心的神秘集體失蹤事件幾乎就跟所有腐霉和真菌有關。他還不完全明白是怎麼發生的,但他已看得夠多而害怕其能耐。他們的補給品位於升降梯井底部,而在他帶下來的八個人之中,就只有他和布里奇存活。
「全死光了,沒有黃金,」布里奇愁眉苦臉地喃喃說著。
「說得太對了,」馬科姆同意道。
他們該繼續還是回頭?如果他們現在離開,馬科姆就得向凡絲報告說他找到少許答案以及更多問題。如果有市中心以及陽光灣小隊的倖存者位於地底某陰暗處,他將讓他們自生自滅-而且有些人還是他的朋友,他們沒有任何人該被拋下。況且市中心將空無一人,雖然不是不可能,但也將難以招募新礦工;誰會想在一個前居民集體失蹤的地方工作呢?要是無人採礦,那麼將不會有金錢流向莽霸聯盟,而脆弱的經濟體也遲早會瓦解為舊時的海盜艦隊世仇。
馬科姆一直喜愛他在航行、導航,以及自由地飛越翻騰海浪並穿過陽光與風暴的時光。感受奪走嬌生慣養的商人的貨品,以及奪去敵對海盜性命所帶來的刺激。但在大戰過後,他幾乎輕鬆地進入一種更穩定的生活。此刻要失去那種生活 …這可不能輕率地考慮,尤其是當他還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尤其是當他選擇不要放棄並且可能拯救這些人的時候。
「你怎麼想,布里奇?」馬科姆靠在隧道牆壁上問道。「我們要折返然後活著搞砸另一天?還是我們持續下探未知之地?」
布里奇脫下帽子並搔抓著頭,然後聳了聳肩。「沒有礦坑,就沒有黃金。」
「還有其他礦坑,」馬科姆說。但老實說,沒有任何一個的規模與產量比得上市中心。「無論如何,死人花不了金幣,對吧?」
那麼,就這樣了。他幾乎要說服自己離開。凡絲可以派某個人來-許多的某個人,馬科姆能夠推薦。不過那可能導致更多人被轉變為 …他伙伴們的下場。
升降梯井中的微弱光芒吸引了他的注意。馬科姆奮力站起身並探出隧道邊緣張望,一邊用手握著他的劍柄。
真菌攀上了牆,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生長著。黑色捲鬚形成了綻放出各種蘑菇的環狀網絡,有些小型如羽狀,其他則分層如階梯,甚至有的長成脊狀如珊瑚。即便他已感到反胃,這個效果既混亂又詭異地美麗。
有些捲鬚的移動方式宛如紙張上的墨跡。隨著馬科姆持續觀看,他發現這些真菌正在組成文字,但卻過於陰暗而無法辨識。慢慢地,這些文字開始發出與他失落的伙伴身上相同的噁心綠光。
安全,第一個詞寫道。然後是,下面。
這是一份停戰協議,還是一個陷阱?馬科姆無法確定。不過他現在知道無論做了什麼,這些東西都是具有感知能力的。若是如此,或許外交手段還能派上用場。或許市中心的居民真的還活在下方某處,而且他能夠安全地救出他們。
希望是一種最危險的武器,馬科姆感覺到它滑過肋骨之間直抵他的心臟,宛如刀刃般鋒利。

阿瑪利亞
沙礫擠壓著阿瑪利亞的身體,既濃密又沉重,比水更糟。細沙滲入她的衣服、她的鼻子,甚至她的嘴巴和眼睛,就算她閉緊它們也無濟於事。她隱約想起曾告訴凱瀾要憋氣,而她也這麼做了。她憋得愈久,她就愈納悶是否她的吸血鬼特質會保護她免於窒息-無論她是否會被永遠困在這條沙河中,無法死亡,無法啜飲那賦予生命的鮮血。
彷彿受到她的恐懼召喚,預視再次吞噬了她。
那扇佈滿雕符且呈現圓形的神秘門變得比以往更清晰。它被裝設於一面洞窟石牆中,其銅質表面帶有綠色的腐蝕痕跡。
一座充斥著淡紫色雲朵的天空,在天空之上卻是 …地面?就像有人在她上方某處舉著一份遼闊的地圖,上面描繪著所有代表地形的顏色,有綠色、棕色、藍色與雪白。
有一顆如太陽般燃燒的明亮圓球-那就是太陽嗎?不可能。它周圍飄浮著怪異的金屬殘片,讓阿瑪利亞想起了破碎的鎧甲。有更多殘片在後方拖行著,宛如來自一場船難的殘骸,一邊發出紫紅色光芒。
來我身邊 …
阿瑪利亞周圍的壓力突然減輕,轉為一種墜落感。她毫無預警地撞上水面,同時也張開了眼睛。他們是怎麼抵達海洋的?不對,這是淡水。暈頭轉向的她朝錯的方向游去,游向看似一座城市之處,接著她才發現那些建築位於水底。她轉身朝反方向踢水,終於衝出水面大口喘氣。在她周圍,其他人也做了相同的事,包括凱瀾,這讓她鬆了一口氣。
他們沒死。她一直都確定豹族打算殺了他們所有人,然後那池流沙就可以派上用場,但他們卻再次存活。純粹好運嗎?還是阿洛佐茲的意志?
就在她能感受更多的寬慰情緒之前,他們周圍的水域出現一陣騷動。是川流使,有幾十個,全都裝配著他們那怪異的玉製武器和元素魔法。
「不要挑釁我們,」其中一位人魚說道。「安靜地跟隨,否則你們將被強行制伏。」
維托出聲咆哮,而巴洛梅則擔憂地看了他一眼。毫無疑問,試圖在川流使的領域裡對抗他們並非明智之舉。
凱瀾咳了一聲並游向阿瑪利亞。「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一天之內被突襲三次,」他哀傷地說。
阿瑪利亞噗哧一聲地笑了。「小心別讓這成為一種習慣。可能會很難擺脫。」凱瀾咧嘴一笑並戲謔地用水潑她,接著在人魚的驅趕下,他們便跟著其他吸血鬼們游向岸邊,前往一份未知的命運。